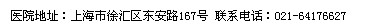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饮食 > 我去非洲做农业
我去非洲做农业
北京治疗白癜风多少钱呀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zn_bjzkbdfyy/
从牛津到麦肯锡,再到两年前搬到肯尼亚,在AGRA(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一个致力于推动非洲农业体系转型的非政府组织)推动中非农业合作。套用之前乐天行动派另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人在世上走一遭,遇见些喜欢的东西,做一些喜欢的事,实在是太自然不过的追求。”
走出去,与世界碰撞
山本耀司在一个采访里说:“一个人的自我,是在关系的碰撞中形成的,厉害人物,是和厉害的东西去碰撞,也要敢于深入你黑暗的潜意识深处,这样你才能看到更多。”在牛津一年的求学经历,是我,第一次与整个世界实实在在的碰撞了一次。
在牛津,同一个项目和同一个学院里的同学动辄来自几十个国家。每看到同学在饭桌上为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争得面红耳赤、或是在模拟联合国上假装自己是国家领袖滔滔不绝时候,我一开始也会暗自发笑。明明一群乳臭未干的学生,却操着国家元首的心。但渐渐的,这对我的世界观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认识到自己不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是作为一个“地球人”存在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地球存在,这也就意味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件是与我这个个体丝毫无关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千年前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过飞机十几个小时的航程,当地球另一边的火山爆发10分钟就报道在因特网上,“天下”变得比从前更近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关心“天下”的事呢?
初遇非洲,遇到的都是问题
毕业后,我加入麦肯锡,这给我提供了一个积极参与“天下事”的最佳平台,让我有机会参与了多个政府和公共领域的项目。年,我借调到盖茨基金会做了一年战略官。在疟疾项目下,我第一次来到非洲。在16天里走过了四个非洲国家,从中央层面的健康卫生部,到边远村落里破破烂烂的卫生站。看到了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制从上到下的种种问题,一环扣一环。
在赞比亚,我们在国家疾病防控中心考察,防控中心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赞比亚充满野心面面俱到的疟疾防治计划,却无奈的告诉我们要实现这个计划,未来三年内至少面临着万美元的预算缺口——我们问: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极度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发展重点,合理分配资源?
当来到疟疾流行严重的铜带省(Copperbelt),我们了解到因为缺乏有效的最后一公里物流,援助机构提供的快速监测试剂、蚊帐和药品迟迟无法及时送达基层——我们问:如何在农村道路稀缺、物流成本昂贵的情况下,准时又低成本的把药物送达?
为了解药物的供应模式,我们又来到村卫生站,看到几名卫生员自发自愿的牺牲自己的务农时间,为当地居民递送药品,而村卫生站给到的补助仅仅是一辆二手自行车,甚至没有任何工资和补给——我们问,这样的推广模式可复制,可持久吗?
在走访中国驻赞比亚医疗队时候,我们了解到,许多在赞比亚开采矿藏的中国公司,在外派员工时缺乏卫生教育,使采矿带成了疟疾流行的重灾区——我们问:赞比亚政府如何联合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共同制定防疟战略和实施措施?
在赞比亚实地考察疟疾项目
在实地考察后,我看着自己满满的笔记,记下的都是我看到的问题和瓶颈。我反而对非洲消除疟疾战略更迷茫了。
“你们要怎么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得知我在盖茨基金会工作,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全球健康这个词实在太大、太宏观太面面俱到。而我从盖茨基金会那里学到的,我们要做的很简单:问“正确”的问题,并尽全力基于数据和证据回答问题。
就好像Jacqueline在TheBlueSweater里说的那样:“正因为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贫穷从来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必须要以巨大的自制力和深深的谦逊心认识到,没有一个人能够一次性给完美的解决方案。
Pooreconomics《贫穷经济学》的作者AbhijitBanerjee就以疟疾蚊帐为例,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一顶五年有效的杀虫剂浸泡蚊帐应该定价多少钱,能够在长期内保证更多的人口购买并有效使用蚊帐?”是免费发放吗?答案却没有那么显然。免费发放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当地居民会不会因为是免费发放的蚊帐而不加珍惜或错误使用?有一位经济学家,就蚊帐的定价做了大量实地研究,通过数据和对比试验找到了最合适的价格区间。这就是贫穷经济学。
在非洲浸药蚊帐是预防疟疾的重要工具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盖茨基金会里的同事,除了多年从事国际发展的资深人士,来自药企和研究机构的专家,还有许多“战略咨询顾问”的缘故。如何将大的命题拆分成正确的分支问题,通过收集和证实数据,并从数据中有效的提炼出结论,并且辅以相关的分析,从而给出切实的建议。这不仅在生产汽车或者设计App的时候有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也是一样的。而盖茨基金会则是这方面的领头者。
从年起,盖茨基金会每年9月发布的Goalkeeper报告,就是这样一份在抗击贫困的战役中,发现关键问题、寻求最有前景的解决方案,评估效果并推广最佳实践,来帮助加速这个进程的“战略咨询报告”。
点击图片查看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投身非洲,农业机构里的唯一中国人
在为基金会制定“中非战略”的一年时间中,我渐渐意识到,非洲不仅存在着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存在攸关世界未来的巨大潜力,毕竟,非洲人口年龄中位数只有18岁,在全球其他地区老龄化趋势持续加剧的大背景下,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
但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都生活全世界最贫困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这里不仅生育率高,失业率也非常高,人口,这个在其他地区都与“红利”紧密相连的词,在这里既可能成为“资产”,也很可能成为“负债”——如果能够对这一地区加大投入,进行更多切实可行的支持,非洲的未来,将改变全世界未来的面貌。
从牛津求学时就种下的“天下事与我有关”的小小念头,在经历过麦肯锡的磨练,盖茨基金会的实践后,终于在此刻开花。年,在结束了在盖茨基金会的借调生涯后,我做了一个在别人看起来有一些疯狂的决定,就是搬到肯尼亚,加入了一个非洲的非政府组织,AllianceforaGreenRevolution(AGRA),从非洲自身的角度出发推动中非合作,增强非洲国家的议价能力,在“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之间找到平衡。
AG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