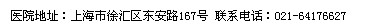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饮食 > 在海地人的头上买药,吃到避孕药还是假伟哥
在海地人的头上买药,吃到避孕药还是假伟哥
在海地,太子港的街头从来没有宁静过。
两缸的力帆摩托发出轰鸣,一个女孩把右脸紧贴在Lecty黝黑的背脊上,她的脚踝上栓着一只红毛公鸡,轮胎撵过的泥地一地鸡毛。
女孩从他宽大的肩膀后探出头,看到一排高耸的脚盆,在随着攒动的人头起伏着,她指着其中最高的一个说:“就是他了。”
黑瘦的小贩左手固定盆底,右手抠住盆沿,把脚盆从头上取下来,“你要什么?”
Lecty凑近一点,“避孕药。”
小贩扫了一眼张望的女孩,利索地从桶顶掏一把剪刀,抽出一板六角形的蓝色药片,剪了一颗,“Cytotec,古尔德。”
古尔德(Gourde)是海地官方货币,古尔德差不多人民币15块5。
Lecty摸出两张古尔德,把小小的药片揣进裤兜,又在旁边的摊上买了一根炸香蕉递给后座的女孩,公鸡已经不再扑腾,蹲在泥地里咯咯叫。
他跨上车扭动钥匙,摩托的发动机声和公鸡不合时宜的打鸣混在一起,往远处彩色的房子驶去。
年地震重建后的彩色海地
在海地,街头兜售药品跟卖油炸香蕉和陶器水罐没什么区别。
首都太子港的铁市场里,举着塑料桶的小贩穿梭在卖活乌龟的巫师和卖山寨Sneaker的摊主当中。
他们把数百种药片绕着塑料桶或者洗脚盆一圈圈排好,再用橡皮筋固定,顶上插把剪刀,创造出一座座整齐有序又错落鲜艳的移动化学巴别塔。
药桶的高度决定和鲜艳程度是确保销量的最大竞争力。
药贩子LaurentDelva已经扛着药桶在街头游走了20年,他的生意总是络绎不绝,诀窍就是把青霉素放在泰诺旁边,这样一眼望去,粉红色的药片和蓝色药片能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如果药桶不够扯眼,根本没人来光顾。”Delva说。
Delva一直以手持电话机,头顶药盆子的形象站在街角,这是他在现代社会里的谋生法宝,“很多人都靠巫毒草药治病,尤其是农村地区。城里用草药也用西药,但年轻人现在不信这些叶子了,他们更青睐软膏和药片。”
顶着货品行走是黑人共和国的文化,也是天赋,他们在烈日下把商机稳稳地顶在头上,觅得一片荫凉。
每天都有上百个海地人顶着药品在城市和农村的街头叫卖。
他们通常天不亮就出门,从太子港市中心的药品大经销商那里采集物资,然后找个热闹的口岸,放下家当,跟精心打扮待嫁闺中的女儿一样,把药桶装饰得和像糖葫芦垛,怎么诱人怎么来。
在繁华的首都街头,一天下来,能赚人民币30-60块钱。
也有些药贩子搭着“TapTap”漫游在各个村落之间,他们能抵半个赤脚医生,走到哪里都会被急需蓝色药片的小伙子团团围住。
"TapTap"是海地的传统交通工具,要下车了,“taptap”敲敲旁边,司机就会刹车。这辆车背后写着"Lifeisnoteasy"(生活不易)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海地人民从未享受到独立带来的好处。
这个南半球最贫穷弱小的国家,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固定工作,75%的人生活在赤贫状态下,某些物价反而高得出奇,3个青椒就要元。
吃喝都成问题,谁还顾得上乙肝、疟疾、伤寒、登革热、艾滋病......更不用说健全医疗服务。
这种加少量黄油、盐和泥巴烙的“泥饼干”是当地贫民的主要食物
海地地震发生后,暴力团伙和抢劫犯蜂拥往商店废墟,掳走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人们冒着受伤的危险,四处在损毁的建筑物废墟中翻找用得到的东西。
地震发生后几天,急需的药物就从药店里消失了。
国际医生Schmidt说,“毁灭的数量超出了压倒性的程度,我去过战区,那里看起来都没这么糟糕。”
海地居民经常一早醒来后,发现街上多了一些尸体,有的是因为偷窃被人群处以私刑致死,也有被便衣警察射杀的劫匪。
如今的太子港还找得到几家高价药店,一旦走出首都,街头贩子的移动药桶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就像地震重建后的彩色房子,在疾病和意外面前,彩色药桶让他们仍旧能看到希望。
药贩子RénoldGermain说,“客人从来不会对我隐藏秘密,他们告诉我所有细节,从痔疮拉血的暗红程度到昨晚秒射的具体时间。不管任何问题,剪一片药就解决了,不行就再剪两片。”
任何一个有药品资源的人都能当药剂师,哪怕对药理一窍不通。按当地的规矩,成为药剂师的资质不是一纸文凭,而是顶在头顶的彩色塑料药桶。
但不是每一个药贩子都能对症下药,鲜艳的色彩下也暗藏危机。
19的Eddy得了痤疮,年轻的药贩子开了抗生素给他。
同样19岁的Nadia曾经在街头药贩那里买了三片堕胎药,想打掉她五个星期大的孩子。
服药后不久,Nadia在医院醒来,这次堕胎并不像药贩子宣称的那样成功。
她先后经历了身体颤抖、大出血、发烧和剧烈疼痛,“我的胃像装满汽油在烧一样。”Nadia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对母亲说。
“在海地根本就没有药品监管。任何处方药都能随意得到。”VladimirLarsen医院产科外的家属,“堕胎药甚至比买验孕纸还好买。”
药贩们不仅从药桶边剪下来路不明的堕胎药,还经常掏出过期或仿制的假伟哥,它们紧挨在一起,没有人知道究竟买的是什么。
仿制药大多来自中国的,假药、过期药来自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
在桶里买药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一样危险,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吃下一片伟哥,勃起48个小时金枪不倒。
37岁的JuleneClerger有5个孩子,她正打算改行去卖香蕉和煮鸡蛋;右边是她的丈夫PelegeAristill,也不准备再干这行了。
这些耸立在肮脏街头的药桶,既像五彩斑斓、令人惊叹的后现代装置艺术,又像这片土地一个个求生故事的映射。
被地震、海啸、疾病和贫穷缠绕的同时,阳光照耀着海面波光闪闪,世界杯期间的街头挂满球队小旗帜和废弃可乐瓶做的装饰,人们在欢腾的竹喇叭声中自然而然地舞动。
海地有句谚语,“层层山外,又是山层层。”不论是从地理还是境遇来看,都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在外来游客眼里,这里和美国夏威夷、中国三亚一样处于最适合度假的北纬18度,同时又是全世界最不宜居的地方。
而亲眼目睹好友的头颅在沙滩上被打碎的海地作家拉费里埃,写了《还乡之谜》告慰更矛盾的真相:我们可以“推翻”曾经的殖民者,却无法改变这片土地上的迷惘和痛苦。
“并不是挨饿就必须吝啬地活着,最具颠覆性的事情或许是,在阴影之下,竭尽全力过得幸福。我花了一生才说出这句话。”
当每一条手臂都拿着枪瞄准你,有只手递给你一盒彩色药丸,一个人蔑视的所有言词,被另一个人的微笑抹去,在两极之间,人必须抉择。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