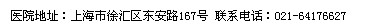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饮食 > 是谁在那里,以管窥你单读
是谁在那里,以管窥你单读
人是寂寞的群居生物,互相孤立,又相互依赖,努力用不经意的方式窥探别人的人生,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早已赤裸地呈现在世上。“我们的黄金时代”寻人计划仍在进行,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来稿。今天推荐的一篇小说,来自刘晗。
可窥的生活
刘晗
人从诞生之日起,面前就会筑起一堵无形的墙。当我们逐渐成长而极力想了解这个世界时,墙上就会主动或被迫地打出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洞孔,并且与日俱增。我们透过空隙窥见别人的生活,以此为奇为乐。此刻,你身边熟悉或陌生的人也会在经意或不经意间管中窥豹,而你却全然不知。直到墙上的洞孔多到让他人不去俯仰,即可看到全部底细,赤裸的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即将面临的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1
直到现在,那个年代空气中弥漫的气息,还在孔盼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当然,还有时代留给他的后遗症。
他总在夜里沉浸在那些神秘深邃而又勾起他内心深处恐惧感的梦魇中,就像一只大手揪起他的心脏揉捏,难以言喻的痛楚。他期盼这种感觉的到来,而且惶惶不可终日。
梦中,他看见红卫兵开着红色康拜因驶向他家,在不远处停下。他绕过他们的视线,拿着从教室偷来的粉笔在墙上写“毛主席万岁”,又怕住在隔壁的红小兵阿生看到他,便畏畏缩缩把字写得飞快。
或许是写字时用力过猛,或许是听到屋内传出的震耳欲聋的惨叫时惊的一哆嗦,粉笔断成了两截。他猛冲到家,家具七零八落,镜子也摔得粉碎。他用手扯开从房顶飘落下来的绿色的、粉色的、黄色的大字报,看到红卫兵正拿着皮带抽打着姆妈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们蓬头垢面,赤裸的躺在血泊中,鲜血从如绽开花朵般的皮肉缝隙中汩汩流淌。红卫兵随手捡起镜子的碎片,朝孔盼脸上反光,肆无忌惮的大笑......
孔盼醒来时,睁眼有些困难,太阳光刚好落在他枕的角度。他嗅到淡淡的雪花膏的味道,知道姆妈在外屋。他摸了摸脸上因睡得太沉而压成的褶皱,想起刚才的梦,真实的难以辨认是否发生过,吓得连鞋都没穿就冲到了外屋。
他看到姆妈正往胸前别毛主席像章,大声问姆妈昨晚有没有看到一辆红色的康拜因,姆妈笑着,用双手抚摸他脸上压的纹理,说康拜因在农村的麦田里才有。他追问,昨晚她是不是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姆妈一下子捂住他的嘴,连连骂他胡说,然后悄声推开门,四下张望。
隔壁阿生家的水壶盖被水蒸气顶的上下乱窜发出钻心的响声,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动静。姆妈回身抱起他说,“不要乱讲,会害死姆妈,让别人听到了,你就再也见不到姆妈了......”
孔盼记得清楚,她说这话时狠狠的攥着他的手,松开时手热的发麻。
学校广播里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从喇叭里咝咝啦啦的噪音中隐约听到忽小忽大的人声。孔盼又迟到了,站在教室外“自惩”。他能预见,只要一进教室,同学们会把所有鄙夷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那种强光几乎能把他的小尊严全部杀死,比阿生对他的咒骂还要有杀伤力。他看到楼道的墙上挂着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就止不住想起昨夜的梦,忽的想起姆妈的话,又立刻断了念头。
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孔盼仍低着头,他不用看就知道,那个满脸皱纹穿着粗布衣服的老太太来找他麻烦了。她的训斥声不但刺耳,而且随着难听的词语四处喷溅的吐沫和口臭味是最难以忍受的。今天,他闻到一种特别的味道,并非姆妈身上清淡的雪花膏味,那是飘荡在空气中若有若无今生也忘不了的芬芳。
她叫颜玉,孔盼班新来的老师。她拉起他的手,让他跟同学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她的手是那么细腻、光滑,同样是穿着粗布格子衣服,她却有不同的气质。从那一刻,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孔盼的视觉模糊、扩散了,他只注意她一颦一笑,刚上小学的他,也只能用美丽来形容她。
放学时,阿生叫孔盼和他一道回家。孔盼一言不发的看着他,阿生推了他一个趔趄,等他刚要追阿生时,颜玉走了出来。他像小狗一样循着那股迷迭香跟了上去,已经数不清拐了多少个转角,记不得这条路离家的方位了。他一度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决定冒着迷路的危险寻找那迷人气息的源头。
颜玉进门,孔盼就潜伏在门外。透过窗帘的缝隙,他窥见她换上一条红裙,露出的白皙皮肤让他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她从军绿挎包里掏出一叠写着大字报的各色纸张,用小刀裁开,几叠几弄的,一眨眼的功夫,被蹂躏的脏兮兮、上面铸着千篇一律看似信仰的经纶纸屑成了几只飘飘欲仙的纸鹤。
正在孔盼聚精会神之时,头被一颗石子击中,回头便看到了阿生。阿生说,要把他跟踪偷窥颜老师的事情和颜老师偷大字报做纸鹤的事都告诉红卫兵,而且他姆妈知道了孔盼姆妈在外面乱搞男人的事情。阿生用小刀逼迫孔盼,让他把这些原原本本告诉红卫兵,这样,有哥儿们罩着,保证能当的上红小兵。
孔盼答应了。
几天后的早晨,他被一阵吵闹惊醒,似睡似醒中隐约嗅到雪花膏的味道,觉得妈妈一定在外屋。走出去时,屋子静静的。
上学路上,他看到红卫兵驶着的卡车上堆砌着他们的战利品——几个戴着高帽子的人站在上面。有两个人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她们脖子上戴有写着“破鞋”和“打到小资产阶级”的牌子,是姆妈和颜玉。
孔盼再也没见过她们。
阿生说,“你没了妈,满世界都是牛鬼蛇神,跟我混,我帮你干掉骂你的洪水猛兽。”从此,他便见天和几个野孩子混在阿生身后,在无数次小偷小摸中苟且偷生。
孔盼问阿生,为什么他当不上红小兵,阿生说,“呸!你净干些见不得人的事,还想当红小兵!”
2
姆妈走了很久,屋里还时不时飘出雪花膏的香味。依旧是阳光洒在床上的早晨,只是那窗帘已被晒的脱了色。自从姆妈走后,窗帘就再也没摘下来,愣是从乳白色晒成了鹅黄色,大块的屙痢印清晰可见。那是他儿时的印记,记得姆妈一看见就发笑。孔盼眼睛潮了,任凭眼泪一直流到喉结。
阿生搬家了,要从昏天黑地的筒子楼北上到首都,整个小城都沸腾了。临行前,他和孔盼去了常去的废旧工厂,阿生说,他家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终于要离开这小的快憋死人的地方了。他言语中流露出的霸气俨然一位身居要位的领袖,回声一波波在空旷的工厂里徘徊。
孔盼看着阿生的身影渐行渐远,直至化成一个小圆点。他打开阿生留给他的快散了架的皮箱,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箱子下压着一块红小兵袖标。他想,阿生把整个童年都留给这个小城了,一丝不剩。
筒子楼并没有因阿生家的离去而变得沉闷。他们前脚刚走,邻居们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有说阿生爸卷走了工厂的钱,还有说阿生爸糟蹋了厂里的女工。更离奇的,说他杀了工厂的会计,把她铸在水泥管里。这些传言都是邻居东方幸子奶奶告诉他的,孔盼心想,这些话也就是邻居们嫉妒阿生家去过好日子,茶余饭后发狠随意说说罢了。
东方幸子,这个有些日化的名字,让她在“文革”受尽了折磨,耳朵被红卫兵的打骂声震的半聋,得了白内障,疯疯傻傻,到处认儿子。她唯一的儿子去插队一直没回来,整天以泪洗面,近日又加了咳血的毛病。她逼着孔盼给儿子写了无数封信,孔盼写的信比他上学时写的所有字还要多。一写到地址时,她说写上“北大荒”就能收到。
阿生走后,孔盼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街上也变得平静多了。街道给他找了一份邮差的营生,他骑自行车奔波于小城周边,晚上累的倒头就睡,时间也变得飞快。他想在急速的飞逝中看到恍如隔世的画面,就猛蹬一阵子车,原本贴了大字报的墙被白圈里面写着“拆”字的墙所替代,他就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孔盼每当想到这些信装载着人们在这些年的生死离合,报忧多于报喜,就奋力快速蹬起来,但结果常常令他失望。信件大多找不到主人,投不出的信几天就堆成了山。
他绞尽脑汁想办法处理掉这些累赘,这比上学时编逃课的理由还难。他听见门外邻居家的水壶盖子被水蒸气顶的上下窜动发出吱吱的声音,想起那个寂静的早上,灵魂出窍的一瞬,注定他以后更忙碌了。
很长一段时间,孔盼每晚只拆看那些信。为了保持信的完好无损,就用水壶的热汽把信封封口处嘘开,看完再原封不动的封好。他窥见怨恨、责备、咒骂,也看到思念、爱慕、忏悔,几次他都想把这些信一并扔到江中,但那个念头一闪即过。他想看每一个真情流露的既是虚构也是现实的故事,毕竟,这些言语距离他太远,但又活生生的存在着。直到他撕开一封写着“转给东方幸子”的信中信,信上说,他儿子得疟疾病死在北大荒。
他拿着信,走向隔壁,门虚掩着。东方幸子躺在床上,她听见门吱呀的开了,小声呻吟、呢喃着。孔盼听见那颤抖的呼唤声,眼泪顿时模糊了双眼,他不敢走到她的身边。
他屏住呼吸,尽量学着成年男人浑厚的声音,哽咽着说,“信.....我收到就赶回来了......姆妈!我好想您......!”
3
老太太临闭眼前,睫毛上还挂着泪花,孔盼把她的泪摸干,把替她写给儿子的信在送葬前放在了她的手上。孔盼想,老太太走前没留遗憾,她见到了“儿子”,现在到了阎王那,这些信就帮他们认认亲,来世再做母子。老太太在亲人的陪伴下离世,而姆妈走前,孔盼看到的只是像风一般的幻影。
时间长了,他觉得这样偷看不知何时是个头,一封封拆信已经让他觉得厌烦。孔盼开始讨厌自己,他不能像老太太那样为等她儿子回来,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
孔盼辞了工,冲到澡堂去晦气。淋浴喷头溅出的让他应接不暇的水花重重砸在头上,任凭热水在脸上、身上肆意流淌,心里山崩地裂,山洪汹涌。他想在水汽蒸腾中洗清一身的罪恶和污秽,捂住眼睛,他看到的却是一道光明。
“啊......!”
一声女人的尖叫就像一把利剑刺入了孔盼的喉咙。一个同样赤裸的女人站在他面前,在热气的氤氲中,孔盼又嗅到了那久远的芬芳,近在眼前。
“颜玉!”
孔盼唤着压抑在心底已久的名字,沉入那松软的令人陶醉的肌肤中,那女孩的身体仿佛在他拥抱下而变得脆弱。他再次看到这张脸,一下愣住,她并不是颜玉,而这张脸也足够吸引大多数男人的目光,何况是现在赤身裸体的完全暴露在他一个人面前。这个女孩此时更像安静的睡在他的臂弯里,没有任何受到惊吓的痕迹。她的昏倒让孔盼慌乱了手脚,吓得一身冷汗,拿上衣服,拔腿向外跑去。
几天后,孔盼面对着一屋子婆姨,一身晦气让这潭浑水刷洗的越发污浊了。这帮脸上布满黄斑和皱纹的婆姨们把他紧紧包围,每个人如咆哮般的话语仿佛龙头里的水无源无尽。
这时的孔盼如落难的蚂蚁,如临大敌,一滴口水就能把他淹死。他耳廓里传来了排山倒海的“嫁”、“娶”的字眼,一声大笑让噪音戛然而止。那女孩正朝孔盼做鬼脸,在她脸上洋溢的笑容有如她的心灵一样干净,完全看不出她是个智障。
纯真最终还是敌不过世故和媚俗,窗上贴的大红“囍”复杂的勾回结构如绳索捆住了孔盼的手脚,无情的扔进了深渊。
每晚烛光亮起,就是一丝希望在闪耀。她有时听不懂他的话,像活在另一个世界。孔盼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她听,她也流泪。在孔盼眼里,她和常人没两样,甚至更懂他。两个人的日子多了欢笑,与日俱增的经济负担也让他觉得不能只靠变卖家产过活。他几乎把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忽地发现柜子后竟藏着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那不再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让他回到了三十年前,阿生——他在哪里?
从县城出发,夫妇俩背着一身家当随着火车颠簸了五天才到达首都,肩上挎的、背上扛的,手上拿的,被逆行的人撞的乱七八糟,媳妇吵着让孔盼背,闹得他心烦意乱。阿生在信里留的地址,孔盼左寻右问才找到。他拉着媳妇走进潮湿的地下室,迎面走来的人们大多面无表情,一脸窘相。
几天后,阿生来拜访,他们互相望着,话少的可怜,显然这些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日子让他们变得生分。阿生送来一个铁艺相框,孔盼随手就摆在了桌上。
孔盼一到这稠密之地,人就如上弦般忙碌,这里的空气的确比家乡古怪,毕竟聚集了大部分自愿出卖贱命的人在此流汗劳作,可想而知。媳妇终日被反锁在家里,直到一天,孔盼回到家,空无一人。
发了寻人启事,半年杳无音信。
没了媳妇,没了指望。孔盼不想回家,但他的脚又不听使唤的走到了家,桌上的一盘小录像带和一张信纸把他的目光吸了过去。那笔体再熟悉不过,阿生说阿爸贪污挪用公款多年,在被捕的前一晚自杀,姆妈也去了,他要把父母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还说那个铁艺相架上加载了一个小型录像机,再也无祝福和挂念之类的话。孔盼在一家店把小录像带放入机器,他和媳妇吃饭、笑谈甚至拥吻场面的重现让一个大男人在众人面前情不自禁的啜泣,阿生这个偷窥狂给他这个震惊的礼物让他感到,错误的遇见,如今却是他最完满的怀念。
4
孔盼漫无目的的走着,仿佛忘记了白昼和黑夜。他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穷酸文人,文人说,他这一生辜负了三个最爱他的女人,自己为她们吃尽了苦头,曾被误判锒铛入狱,但和她们的误解最终都未能化解,他想把这些写出来,可惜视力一天天的锐减,快失明了。
孔盼似乎找到了知己,上辈子一夜间又回来了。他把角膜给了那个文人,因为他能行云流水的写出他们的故事。在他看来,他给的不是角膜,而是一个男人成长的私密史。
失明之后,孔盼只要听到走廊里传来高跟鞋铿锵有力的回音,他就想,那可能是姆妈、颜玉或是走失的媳妇,她们读了他的故事,来看他了。
刘晗,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散见于报纸杂志,曾入围台湾第五届林语堂文学创作奖小说组决选,获得香港第三十八届青年文学奖新诗高级组优秀奖,第三届大学生影评大赛研究生组二等奖。
《可窥的生活》入围台湾第五届林语堂文学创作奖小说组决选,收录于《第五届林语堂文学创作奖作品集刊》,林语堂故居出版,年12月出版。
征稿还在进行,活动将在7月6日截止,欢迎继续来稿
征集内容:不限形式、不限内容
投稿邮箱:youngcreativity
.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医院治白癜风好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