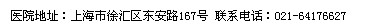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预防 > 基因黑客下
基因黑客下
最近,布罗德研究所58岁的主管埃里克?兰德告诉我,“我最喜欢CRISPR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取出任意一个癌细胞系,敲除每个基因,识别出每一个细胞的阿基里斯之脚踵”。兰德是人类基因组项目领导之一,他说这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有前途的研究工具。他说,“你还可以用CRISPR来系统地研究癌细胞逃脱治疗的方式。这使得我们可以绘制一张综合的癌症路线图。”
兰德继续解释道,肿瘤的每一个弱点都能够被一种药物攻克。但癌症细胞用多种方式躲避药物,为了成功,治疗时需要将所有的逃避途径全部封锁起来。这种策略对类似艾滋的传染病来说已经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记得对艾滋的悲观情绪吧”,他提到了早些年的艾滋横行的时期,当时诊断就意味着判了死刑。最终,病毒学家研发出了一系列的药物,能够阻碍这种病毒繁衍的能力。疗法成功了,然而,只有当这些药物一道工作时,才能完整地阻止这些病毒。同样的方法成功应用于治疗结核病。兰德确信,它也能够治疗很多癌症的:“利用三倍药疗法”治疗艾滋病,“我们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们输锝很惨,但某天,突然我们就赢了。”他站起身穿过办公室,走到书桌旁,指着墙描述着他对未来癌症治疗方法的愿景。他说:“将会有一张很大的图表,当然,是电子的,它会包含针对每一种癌细胞的治疗途径---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你能打败它们的所有方法,它们能够逃之夭夭击败治疗的所有方法等等。当我们有了这张表时,我们就赢了。因为每一个癌细胞刚开始都很天真,它不知道我们的冷库里等着它们的是什么。传染病则不同;它们传染的过程共享它们所知道的信息。随着它们从一个人迁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会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但每个人的癌症刚开始都很天真,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够战胜它的原因。”发展任何像CRSPR这样既复杂又有广泛应用的技术,需要很多科学家投身其中。围绕发明和许可权的专利斗争非常普遍。张锋、布罗德研究所和MIT现在就卷入了这样一起纠纷,与詹妮佛?杜德纳和加州大学起了争执。杜德纳是伯克利大学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年,她与在德国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研究病原体的医学微生物学家艾曼纽?卡彭特及其领导的实验室一起第一次演示了CRISPR可以编辑纯化的DNA。他们的论文于当年6月发表。然而在年1月,张锋和同时供职于哈佛医学院及MIT的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证明CRISPR可以用来编辑人类细胞。现今,专利通常会授予第一个提出申请的人---在这里当然是杜德纳和卡彭特。但张锋和布罗德德研究所据理力争,认为早期关于CRISPR的成功并没有涉及该技术是否能够用于复杂的生物体,而这一点对科学家寻找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方式影响深远。张锋被授予了这项专利,但加州大学要求官方重新进行评估,而最终裁决尚未公布。他和杜德纳均跟我说这个官司让他们分了心,希望能早日解脱。两者都保证将向研究员们免费开放所有的知识产权(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但两者也都涉及到一些新公司,这些新公司和其他很多医药公司以及盈利企业一样,想要将CRISPR技术用于治疗。CRISPR研究变成一项大事业:许多风投公司互相竞投数百万的资金,并且任何专利持有人都有权收取数额不菲的专利许可费。谁在这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谁就能猛赚一笔。其他成果同样有份,甚至可能包括诺贝尔奖(杜德纳的支持者认为她将是美国下一个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宣传战似乎有点类似于奥斯卡金像奖季节的电影制片商之间的勾心斗角)。就在去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名张峰最有声望的成就奖,认为他的基础研究为消除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其他脑科疾病“指引了一个方向”。几个月后,杜德纳和卡彭特每人收到三百万美元的突破性进展奖。该奖项成立于年,由硅谷一些亿万富翁资助,每年颁发给取得科研突破成就的科学家。这两位女士还出现在《时代周刊》年度百名世界最具影响力者的名单上。事实上,这两个研究团队都不是最早证实CRISPR,或拥有第一手资料解释说明它的工作机制。年12月,日本大阪微生物疾病研究所的生物学家们发表了从普通肠道细菌---大肠杆菌中获得的一个基因DNA序列。在早期染色体研究时代,世界上数千所实验室曾开始尝试去勾画从果蝇到人类的广泛物种基因图谱。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特殊基因的功能,日本科学家对其周围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当他们分析完数据,惊讶地发现一个他们谁都不认识的基因结构。他们对于导致这些奇怪现象的原因毫无头绪,但他们记录了它,发表于《细胞学》杂志的论文,最后一句注明:这些基因序列的生物学重要性尚未可知。这个谜团一直保持到年。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莫西卡长期探索理解CRISPR,决定将其DNA跟数千个类似生物体的DNA进行比较。结果使他震惊:每个未知序列结果都是一个入侵病毒的DNA片段。研究的速度加快了。年,任职于丹麦食品公司Danisco的微生物学家鲁道夫?巴兰高和飞利浦?霍瓦特发现,他们的一部分酸奶通常会被一些病毒所破坏,而另一些却不会。他们决定找出原因,科学家们用两种病毒去感染生产酸奶的嗜热链球菌,结果发现大部分嗜热链球菌都死掉了,而存活下的那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受到了CRISPR分子的保护。“独自一人不可能发现这些事情”,当我们在哈佛医学院乔治?丘奇的办公室里见面时,丘奇告诉我,“整个专利权之争是非常愚蠢的。里边有很多研究成果。如果有任何人应该对这件事小题大做的话,我也应该小题大做。但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很好的研究者,他们全都在做这项重要的工作,争来争去完全就是小题大做。”从那一刻,当修改基因变成了可能,很多人,包括那些参与实验的人,都被这一想法吓坏了:那些穿白大褂的科学家们将要重排生命的基本要素。年,当时在MIT就职的分子生物学先驱大卫?巴尔的摩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伯格一道因对病毒遗传学的基础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呼吁暂停基因编辑研究,直到科学家们开发出能处理包含重组DNA生物体的安全法规。这次会议于年,在加州阿西洛马的会议中心举行,此后该会议被当作生物技术的制宪会议。与会人员约名,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讨论限制偶然释放转基因生物风险的方法。与此同时,创造“设计婴儿”的可能性还太遥远。这只是一种展望,不管多不可能,这种展望和所有关于CRISPR的记述牵扯到了一起。然而,这项技术似乎太让人震惊。在坎布里奇,麻省和哈佛的所在地,市议会几乎将这样的研究全都禁止了。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但解码DNA序列并不容易。“年,30组碱基对(即组成我们DNA的60亿核苷酸双螺旋链上的30组),就是好几年的工作量”。乔治?丘奇告诉我。而现在,同样的工作仅需几秒钟。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CRISPR的最大影响将是能够协助科学家快速重写动植物基因组。在实验室里,农业公司已经开始使用CRISPR来编辑大豆、水稻、土豆等的基因,使其更营养、更抗干旱。科学家们甚至能编辑基因将过敏原从花生等食物中移除。通常,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让基因变化传播到整个物种。这是因为,在有性繁殖时,任何基因的两个版本都只有50%的几率能遗传下去。但“基因驱动”(根据其在很多世代推动基因的能力而命名)试图凌驾于传统基因学规则之上。由CRISPR在染色体上改写的变异能够在每一代都进行复制,因此几乎每一个后代都能遗传这种变化。例如,给一只蚊子进行一次基因变异,使它无法携带引起疟疾的寄生虫,那么在一两年之内,大部分蚊子都会被改变。如果这种变异减少蚊子产卵的数量,那么这一物种将会逐渐灭亡,连同它所携带的疟疾寄生虫也将一起灭亡。凯文?埃斯韦尔特是哈佛大学的进化学生物学家,他是第一个演示基因驱动和CRISPR可以联合起来改变野生物种的性状的人。最近,他开始研究利用该技术重写野生老鼠的基因以消除莱姆病的可能性。莱姆病由一种细菌引起,通过扁虱传播,在叮咬过老鼠后,有超过85%的几率会感染。然而,一旦被感染,某些老鼠自然地就会获得免疫力。埃斯韦尔特说:“我的想法是获取已有能抵抗莱姆病的基因,并确保所有的老鼠都有最有效的版本”。为了做到这一点,科学家们将会系统编码紧靠CRISPR系统的最具保护性的基因,并使其聚集在一起。埃斯韦尔特强调这种方法只有在大量实验和无数次关于该过程利与弊的公众讨论之后才有可能实施。CRISPR研究的进展几乎每月都在更新。最近,丘奇报道他在一个猪细胞中同时编辑了62个基因。如果这个技术精确且可轻松复制,那么,将大大缓解美国器官捐赠的恒常性短缺。近几年来,科学家们试图找到用猪器官进行移植的方式,但是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猪的DNA里含有可传染给人类细胞的逆转录病毒。丘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些病毒拥有一个共同的基因序列。他部署CRISPR到达精确位置,并将其从基因组上剪切出来。这个的实验最成功的地方,就是CRISPR系统删掉了嵌入猪DNA中的全部62组逆转录病毒。随后,丘奇又在实验室将这些编辑过的细胞混入到人类细胞中,并没有出现感染迹象。尽管CRISPR使得改变人类DNA成为可能,但依然存在严峻的风险。詹妮佛?杜德纳就是一位直言不讳的人士,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