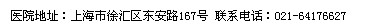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预防 > 毛主席在雩都中
毛主席在雩都中
一走出屋,毛主席的文書黄祖炎、警卫員吳潔清、陈昌奉等同志都围上来,着急地問:“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热度很高。”我簡单地回答了他們一句,就问鍾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鍾福昌说。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儿米汤。”吳潔清说。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头痛得厉害。”鍾福昌说。
究竟是什么病呢?凭征象和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经验,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肠伤寒;一是恶性疟疾。经过仔细分析,想到毛主席的胸部既然正常,虽有几声咳嗽,也不厉害,不见吐铁锈痰,不像肺炎;腹部虽较胀,但经过灌肠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見斑点,也不象伤塞。三个可能否定了两个,我判断毛主席得了恶性疟疾。据了解,雩都这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经有人患了疟疾,再說这时正是初秋时候,在南方是疟疾流行的季节,毛主席的床上沒有蚊帳,可能传染上了这种病。
鍾福昌同志虽然給毛主席吃了奎宁,但药量不够,不济事。我做了这样的判断后,准备給毛主席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我把这意見告訴了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他同意了。我給他打了針,两小时后,又給他吃了一片零点三克的奎宁丸。
我叫鍾福昌給毛主席喝开水,多換換額上的冷手巾,就走出了他的房間。
黄祖炎已经把我的背包拿进他的房間里,房里加了一块木板,搁了个铺,让我和他同屋住。这时我才看了看这所房子。这是一家老百姓的住房,一连三間,左边一间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中間一間是个厅,警卫員同志和鍾福昌住在里面;右边一間就是黄祖炎住的。除了厅稍大一点儿,两边两間都很小。我走进黄祖炎的房間,坐到鋪上。黄祖炎一边帮我解背包,一边說:“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可把我們急坏了,鍾福昌的药又不頂事。”
我躺到铺上,說:“沒有化验仪器,这病是不大好判断。”
“是疟疾?”黃祖炎問。
“恶性疟疾。”我說。
“这病好得快嗎?”黄祖炎又問。
“会很快好的。”我安慰他,同时也安慰着自己。
我休息了一会儿,心里老不放心,又起来去看毛主席,見他睡得很安稳,呼吸也很均匀。我踮着脚走了出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听到黄祖炎的床板老是咯咯的响,外屋厅里,也不时有人走动。我虽然赶了一天一夜路,但心里不安宁,眼一合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惊醒过来,側耳听听对面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毛主席的咳嗽声,心里就象扎上了針一样,更睡不着了,心想:不知退烧了沒有?我判断的病情不会錯吧?药下得合适吧?脑子里一个劲地翻騰着;有时听不到什么动静,眼皮就合起来了。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毛主席床边,見他已経醒了。我问:“主席,好一点儿沒有?”
毛主席轉过身来,用手摸摸額角,說:“头轻了一点儿。”
我正拿出体温表,要給毛主席試体温,他問:“你睡得好嗎?”
“我睡得很好。”为了使毛主席宽心,我撒了个谎,接着問:“主席睡得好嗎?”
“我睡得好。”毛主席說。
我給毛主席試过体温,一百零二度,退了点儿。我心里很高兴,全身都感到轻快,我的判断是对的。
“热度退了点儿吧?”毛主席问。
“退了点儿!”我兴奋地回答。
我又給毛主席检査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象昨天一样,我給毛主席打了ー針,拿出三片奎宁丸,一天分三次吃。
第三天,毛主席的体温退到一百度,額上的湿手巾拿掉了。当我問到毛主席的健康时,他說:“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儿。”
这天,和前两天进行了同样的治疗。吳潔清給毛主席煮了点儿稀飯。
我回到黄祖炎的屋子里,感到肩上的重担轻了,心里很舒暢。我打了个报告給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的病况,并建議中央和后方的同志吃一点儿奎宁,也預防疟疾。
心里轻松了,睡覚也香了。第四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有个人走到我床前,温和地问我:“这几天你累了吧?身体怎么样?”
我睁大眼晴一看,是毛主席!他怎么起床了?我急忙爬起来回答:“我很好,主席,你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主席笑着說。
我拿起葯箱,随毛主席走到他房中,給他检査身体,一試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銀柱稳稳地停在九十八点六度上(即攝氏三十七度)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全身暖洋洋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我捏住这支体温表,看着里面那一管透明的水銀,它今天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发出闪闪的光彩,我越看越可爱,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感激它的心情,好象它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报告了我一个最好的滑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訴鍾福昌,告訴黃祖炎,告訴吳潔清、陈昌奉,还要报告党中央,讓所有关心毛主席病的同志放下心上的石头吧!
我忍不住心里的喜悅,笑着报告毛主席:“你退烧了,九十八点六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主席也笑了。
这时,我見毛主席已经坐到那张沒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紙、毛笔。干什么?毛主席要开始工作了?那怎么行呢?連烧了六七天,烧得那么高,六七天只喝点儿米湯,昨天才开始喝了点儿稀飯。今天虽然退烧了,两眼已陷了下去,臉上沒有血色,又瘦又黄,走把路来都是轻飘飘的。我是一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況,就是一个鉄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毛主席至少得休息三天!三天!但是,看来毛主席連一天、半天、一小时都不肯体息。他已在翻阅文件了。我一定得尽到医生的职責,劝阻他。
我走到桌旁,說:“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現在就工作太早了。”
毛主席望了我一眼,象是想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严肃而温和地对我说:“体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他見我脸上現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我說:“我好了,你放心吧!”(整理:于都中华银楼店(工贸城文昌路—15号)钟菊香,手机;供稿:于都县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