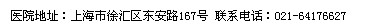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预防 > 山花2016年第8期荐读曾哲不折
山花2016年第8期荐读曾哲不折
曾哲:原名刘增哲,年生于北京朝阳区,原籍河北沧州。年毕业于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年开始发表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全身心投入“漂泊文学”的探索与实践。曾获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北京文学新世界中篇小说奖等。著有长篇小说《呼吸明天》,短篇小说《藏北草原,我的羊皮袄》,诗集《远去的天》,长篇纪实文学《离别北京的天》。
不折不扣之阿瓦山歌·野青
A面我小的时候,常听一首歌:村村寨寨,嘿!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二十多年前,我来到这里。
从单甲乡出发,翻了两座大山,进入了原始森林。浓荫蔽日,青竹披藓,绿纱树挂。过江龙,翠蔓青藤钻来绕去,一条路径,被布置得就跟凯旋门一样。
肖吾,是县中学的体育老师,放了暑假陪我。他人轻巧灵活,会武术。我的胆量,全靠他给壮大。我们在中缅边境号界碑边边上的嘎甲寨子,住下。
水泥的界碑是年建的,齐肩高,竖立在一个土丘上。土丘上的灌木稀稀拉拉,荒草很盛。
肖吾说,当地老百姓有句俚语,是骂鳏夫的:一块界碑,一片荒地,萌不出种子,哭流了鼻涕。界碑,每个佤族人心中都有,然而边境、边界线,却是模糊的。界碑南北全是竹楼佤寨,通婚多了,亲戚也多。相互串门子,如同一个村寨的邻里。
听说界碑外面那一带很乱,听说缅甸共产党在和缅甸独立团打仗。常常听到零星的枪声。枪声在茂密葱茏的上空,像大蓝雀鸟滑过碧天的啾鸣。
这寨子不小,有五六百口人。寨中的土坡中间,长着一棵树冠大极的老榕树,遮荫了几亩地。错节的盘根儿,能坐下全山寨人的屁股。大榕树上,还吊着口已经发黑的青铜老钟。寨佬说,有枪声过了界碑,一敲大钟。过来的人,保准儿像撒开腿的兔子,全吓跑回去。
我的房东家七口人,男主人汉姓陈,佤族名字叫俸诏,女主人叫娥妣。竹楼建在坡坡上,大龙竹梢条稀疏散布,掩蔽了半个楼顶。隔着一层竹篾地板的楼底下是牛棚猪圈,因为天阴潮湿,粪臭臊气钻过篾缝,漾满楼堂。牛铃在楼板下,整宿叮当。
竹楼向南开一小窗,窗扇是草编的。掀起窗扇,竹寨山村的雾雨风景,把我看傻眼。从一个个黑灰色的茅草楼顶看过去,寨坡下是叮咚河流。河对岸不远,有两座凸起的山峰,郁郁葱葱,挺拔陡秀。
寨子里的青石板路,阶阶级级,高低舒缓。打听了半个寨子,我才找到串姑娘的肖吾。告诉他明天我要出一趟寨子。肖吾在竹楼的栏栅里露出半个脸急急地说,去吧去吧!然后就消失了。我怀疑他根本没听明白,自己要去哪儿,到底去干嘛?
我起了个大早,山寨还在沉睡。也没碰上什么人,只有几声鸡鸣,两声狗叫。顺着稻田边上的小路,没想,只十几分钟,就过了界碑,进了缅甸。恰逢一伙没带货物的马帮,赶早路南下,就随了队伍。
山谷中,清脆的铃铛不断。草啊树啦,团团片片簇簇绿绿无法形容。没晨风,早雾浓一处稀一片。一路没打大弯儿,就到了滚弄坝子。
出境不是为了找累作死,是我的好奇。寨佬跟我说了件新鲜事。
“前些日子,从滚弄镇子的南坪寨,来过一对中年夫妇。我们看他俩陌生,拦在寨子间的大榕树下,端来水酒给他俩解渴。女人站着,说啥也不坐。她男人蹲鞧在一边抽着竹筒水烟,也不吱声。她说那年她生了个男娃儿,没得三岁,不仅走路快得像刮风,没歇闲,还一天到晚唠叨不停地说嘴。会说佤话,会说汉话,还说一些他俩口子听不懂的。她男人插言说,是英国人的话。娃儿说,他不是他俩亲生的,他是界碑那边的孩子,住在咱嘎甲寨,咯因(阿爸)叫俸诏,麦(阿妈)叫娥妣;家中有五个姐姐;水牛两头,一黑一黄,黑牛有两个铜铃铛,平时脖子上挂一个,等收稻谷时挂俩;竹楼梯十九蹬;门口一棵樱桃树;楼南一蓬大龙竹。五个姐姐叫什么叫什么,说得明明白白,一点不差。这说的不是别处,正是你的房东家,的确丝毫不差丝毫不差。你说奇是不奇?”
“后来那对夫妇呢?”我问。
“见到你家房东,在竹楼里坐了坐,连茶都没喝一口就回去了。”
听说了这些,我再也呆不住了。心痒痒,脚也痒。
这天晚饭后,我诚心闲闲散散地要咂罐罐茶,留住俸诏老爹。抓这个机会问:“您家五丫头后边,可生有个男娃儿搞丢?”
老爹笑得前仰后合:“瞎,你这北京老师会玩笑哩。男娃儿,那是我天天年年的梦哩。要是有,我含在嘴里怕化,抱在怀里怕摔,屙屎屙尿也不撒开手,还会丢?丢了我自己的毬儿,也不能丢了他。”
我想起欧洲哪个国家,出版了一本叫《时空奥秘》杂志。根据这个杂志调查人员的统计,全球范围内,类似那个小男孩的特异情况,已有三十多例。我搞不清楚咋回事,但有一根儿大青筋,在我的大脑里蹦跳。想过界碑那边,去看看那个小孩,只是看看。
闷热的滚弄小镇子上空,似乎有只无形的大手,在滚弄着一个湿热的气团,抑或像泼洒沸沸扬扬的开水。刚还清凉爽快,倏地又闷潮。抓把空气,能攥出汽水。我和马帮分手后,就住下了。住在录像放映站的小院。
放映站的院墙东接边,是一座小乘佛教寺庙。一天三次的钟声和念经,在录像片打打闹闹的音响里,隐隐现现。院墙的北边是甘蔗地和香蕉林,去北老远,一直铺展延进山谷。院墙西隔着个夹道,是一家榨糖工厂。天气越热,空气越甜,好像压溢出的糖汁有了翅膀,在我的鼻孔四周飞来飞去。院南,面临滚弄镇子东西一公里长的主街。院内,一人高的竹栅栏门边,是我居住的小屋。向东的窗户,夜晚听得真切街上的行人脚步。
镇子上的青壮年男人很少见,街子上站半小时,也很难瞅见一个。这滚弄,是个新奇古怪的地界儿。可我在街子上转悠了两天,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
今晚没放毛片,收场早,可能是因为我到来的原因。
夜风,从香蕉林吹进街子,吹进院子。不仅不爽,还湿腻腻粘糊糊。我想好了,这日子不能久呆。呆长了,咱这么一个地道的北方汉子,会长绿毛的。
能脱的全脱,只穿一条内裤儿,躺倒。有不祥的动静,我惊撑开双眼,正要起身,黑影里有人堵住我的嘴巴,蒙上眼睛。动作之敏捷、之利索,是个老手。
我被几个踮脚小跑的人,双脚冲前,平抬着。前边高后边低,控着脑袋。路好像还磕磕绊绊,几次差点把我掫下去。
这种状态,似乎感觉没持续太久便停住。有人扶着拽着,把我小心翼翼戳立在地。然后解开膝踝的绳子,不由分说按坐在一把椅子上。分开我的两只脚,与椅子腿儿,背靠背儿,上下左右,一同捆了。好嘛,身上手上的绳子还没解开,都加在一堆儿,我这是被捆两道啦。记着,可别小瞧了自己。这样的待遇,也该是个人物才行啊!蒙在黑布里,觉得有几张女人的嘴巴在叨咕,其中好像也有个男人的声音。说的都是佤语,似乎有争吵,有商议。过后有个男人说着什么,走到我跟前,要脱掉我的裤衩。
“嘶啦”,裤衩被刃器划开拽走。最后的遮羞布没啦,廉耻和自尊也一同被扯掉。除了绳子,这回是一丝不挂了。
我的记忆赤裸裸,清晰地镌刻着,每一个细节。
有一只冰凉的手,捧起我裆里的那堆东西。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捧着圣物。一边拂弄着一边说着什么,声音很严肃。过会儿,又换了一只温暖柔软的小手,挟带着一股浓郁的檀香皂味儿,骚扰着鼻孔毛。我实在忍不住,长长打了个喷嚏。就听见女人细声细气的汉话:“不得了,嘴巴好大,大象的一样,牙齿还白瓷儿地呢。”说着,那小手没停止扒弄,翻找着什么,揉搓着卵子。我的阿物,就开始不听话,不老实,探头探脑地张望。
有笑声,那只小手却没离开。说老实话,他们并不是生殖器虐待狂。他们并没有用鞭子抽,用绳子勒,用辣子面,用清凉油。否则我就惨了。只是摸索,很轻很慢。我坐着的是一把竹椅子,松懈惯了,耐不住要动。可一动,就“吱扭,吱扭”地响。椅子上的裂缝也欺负人,咬屁股,夹大腿,又痒又疼。我只好挺直一切,假装稳如泰山。
有人抱着我的脑袋,贴近嘴巴,吸流着鼻子在闻什么。然后又是叽叽咕咕。
忽然声音全消失,消失得极快,如一阵轻风掠过,轻得连尘埃都没扬起。
一切静寂。我心里打鼓,不知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将要继续什么?绳子捆得太紧,只好以静制动。
几十秒钟过后,有人走到我身边。解开蒙着我眼睛的黑布,拽出塞在我嘴里的汗酸背心。面前,是一间空空荡荡的木结构屋子。镇子上这样的房子很多,家家户户都一样,没啥新鲜的。几根儿蜡烛的火苗,飘飘乎乎,照得四外朦朦胧胧。
看见她,我惊愕了,身边竟然站着一个少女。在放录像的小院里见过几次,她叫野青。
野青的母亲早逝,父亲在曼德勒,给做象牙生意的老板当保镖,一年半载说不定哪天回来一次。野青一打小,在界碑北边村寨里的姑姑家住。读了小学,又读中学。开玩笑地说,人家还是正而八经的留学生呐。汉话说得也不错。
“谁把你弄到这里来的?”
“快帮我解开绳子。”我还光着身子。
野青不慌不忙为我松开绳子问:“是谁?”没有一点难为情。
我以为她会满脸通红;以为她会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以为她会忸忸怩怩背过身给我解绳子;……,还以为了一些,但我以为的都没有出现。
她见我不答话接着问:“这是我家的库房。是谁把你整治到这里来的?”
“不是整治,挺舒服的,我是被抬来的。”我开着玩笑,想缓和一下气氛,“也不知惹恼了你们街子上的哪位大仙啦?几天来加上你这么个小姑娘,搭过腔的也不过五六个人。”我穿好短裤,把裤裆里的东西再一次藏匿好,揉揉捆过的疼痛。
野青没轻松,绷着脸,目不转睛。多一眼都不看,好像男人身上没有她敏感的东西。
“到我屋头来说话”。她举着一根儿蜡烛,吹灭了其它,领我出了仓房。
出了仓房,我大汗珠子,呼拉冒了出来。两只手,就得一个劲儿地刮下巴颏,再把汗珠子甩出去。刮了甩,甩了刮,但没用。这叫惊汗,没三两个时辰,是过不去的。
仓房和野青家,只隔着一条小溪。飞身就可以跨过去的小溪上,铺着板凳宽的石板当桥。我没上桥,走到小溪里。夜色下,水是黑黑的,温温的。俩脚丫子蹚了蹚,很舒服,索性把脑袋也扎进去。泡透了自己后,一屁股蹲下,左右开弓往身上一通乱撩,这才缓解了一身的燥热。
野青家屋前的那段路面,有点儿硌脚。野青的木屐,呱哒呱哒,在夜色里很是清脆。
到了她家屋里,我先吃了块西瓜。喘过气,我平稳下来。胡拉着脸蛋上的瓜瓤子,跟注视着自己的野青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想起这儿的女孩子特时髦喝啤酒,就掏钱。兜里的钱居然一分没少,只是都湿了。
野青兴奋得屁股跳离板凳,两手翘着指头,打响了一个清脆的榧子。像孩子一样,从我递给她的一沓钱中,拽走一张拾圆币。甩掉木屐,光着脚,刮风似的跑出门。
野青17岁,中学读完就在家闲呆。一天到晚,晃荡来去,混日子。剃着一个男孩子的寸头,很短,支支扎扎。穿一身浅蓝牛仔装,好像挺厚的,也不嫌热。本来佤人名字中的“野”,代表家中第一个女孩子。但她却像个男孩,浑身上下,散发着的野味儿、野性,恰恰吻合。她一天到晚泡在录像站,看录影。
野青,买回四瓶啤酒。磕掉个盖子托着底儿,她一仰脸,自己先灌下去一半。野青抹了抹嘴巴定定心,稍喘着问我:“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也不清楚!”
“你说个大概齐模样,这镇子就这么丁点儿,一会儿我给你捆来,任你宰割。”
知道她不是吹牛,这孩子的确不一般。“一个也没看清,蒙我那块黑布,叠了好几层,连点儿光亮都看不见。”
“好,大哥你等五分钟,我马上回来。”她又把剩下的啤酒喝干,扔下空瓶子,叮叮咚咚,兴冲冲出去了。
真的,也就几分钟。我的腰杆还没疏散开,她就拉进俩姑娘和一个中年男人。听他们说话,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我认定不是。
野青大喝一声:“滚”。仨人赶紧往外跑,快到门口了,野青又突然喊住他们:“我要的那条活腿,明天一早给我送来。”
“好!好!好!”三个人答应着,步子似乎更快了。
我听着心里直激凌。看着出门的六条腿,问野青:“活腿,他们欠你的?”
“是啊!”
我有点不知所措:“多大的冤仇?烧了你家的房?毒了你家的水?砸了你家的木椿?活腿?摘下后是活的,还是从活人身上卸下来?”
“没那么凶恶恐怖,说的是还没杀的牛。”她把最后的字,加重了语气“但我已经花钱买下了,连着半边屁股蛋子的一条,叫活腿。要是有三条活腿都被人买了,这牛就非杀不可了。我们管这叫,买活腿。”
“你一个人,要这么大一只活腿干嘛?”我有意无意地瞎问。
“给你吃啊!你不知道牛肉烂饭,是我们待客的美味佳肴。”
“待客?哦,我以为佤寨待客的上品是鸡肉烂饭,牛肉烂饭第一次听说。”我接着她的话茬。感到了这里边有些什么蹊跷,有什么东西被我看到了,却一闪而过,没有抓着。
野青说:“大哥,你要还想再往下住的话,就不能在录像站那个是非之地了,多乱啊。”
“那住哪?”
“住我这儿,只能这样!否则从明天开始,每晚你都清静不了。滚弄镇子已经好久没外人来了,你人高马大的,在街上一走,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看你,你知道女人们管你叫什么?叫情种,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男人味。镇上的老男人都羡慕死你了。大家说,让你把种子撒干净,才放你离开。”她看我没什么反应接着说,“其实不会放过你的都是女人,男人只是帮忙搭手的。女人用的武器是甘蔗砍刀,逼你把那根儿东西肏进她的裆里。你不干也行,可以放你一马。但你临走了,她会给你那玩意齐根一砍刀。砍下带走,回家慢慢地享用。”
“还有这等怪事儿?那我就将计就计,决不能被阉割。”我虽然心下惊讶,但还是开着玩笑。没想到,这姑娘竟如此口无遮掩。“你知道我们北京城,过去有这种被阉割的人嘛?叫太监也叫公公。”
“我不知道你说的。可我知道她们今晚这是第一次验身!首先看看你有没有性病,怕你把外边的脏东西带到我们镇子来。以前我们镇子有过,听说恶心极啦,看见的人都吐了。所以,来我们这的好几个外乡男人都给杀了。腿儿快的就跑,东西南北,跑得连路都不择,再不敢回来。其次,查验你是不是抽毒粉吸白面的,我们叫抽10号。抽那玩艺儿的,她们也嫌弃。说和这样的男人配出的种儿,生的男娃没鸡巴,生的女娃没腚沟儿,就是石女。”咚,说着野青给了我胸口一拳,还挺有劲儿。然后又说“你是通过啦。中国、北京,干净。”最后的一句话,她声音高亢起来。而且用汉语、佤语、英语,各说了一遍。
“我的天!”这让我感到又新奇、又好笑、又尴尬、又兴奋。还搀杂着一些,惶惑。
“抓你的女人可能是糖厂帮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们大多是染过性病封了裆的,听懂吗?就是录影带里演的那样,锁住,谁也不准通过了。所以她们满怀一腔怨恨,她们可厉害啦,别招惹她们。她们还有纲领口号,‘为了后代,为了妹妹。’我一般不惹她们,她们也不敢惹我。所以你住我这里,我当你保镖,最安全。”
“让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作保镖,是不是太惨了点儿?”
“我早就想跟阿爸一样,我读书时的远大理想就是当一个女保镖,我这是遗传。长拳、通背、八卦掌,我练了将近三年。都是在那边,跟我中学的体育老师学的。”她歇了一下儿,接着说,“除非你顺从她们!否则这镇上只有我保护你。”停住话,她从床头枕下,抻出把一尺多长的匕首一甩,戳在酒瓶子间。匕首发出颤抖的声响,像一群蜜蜂飞过。
我认识野青的那天,就听录像站的老板说过,野青的外号叫“拼命假小子”。镇子上只要打架,一准儿有她搀和。
我喝着啤酒寻思着,目光绕过瓶子打量着野青。喏,是个真小子模样。短发,圆眼,肤色微黑,挽着袖子,圆鼻头上汗珠闪亮,脸上洋溢着侠肝义胆的稚气。惟一表明她女儿身的,是两个手腕上戴的宽手镯,银白的,有十公分宽。以及卷翘的睫毛下一双水亮秀眼,和一对细腻修长的手。
“我住这里,对你一个姑娘家的影响不好。”我得为她着想。我怕什么,随时走人。
“没事儿,这的人都把我当男孩子看。只有你,第一次在录像站见面,你就喊我小姑娘,我一直记得。就住我这。”娇嗔的语气,让屋中“呼悠”一下,出现了温馨的氛围。
我还是有点儿难为情,无法决定。她不高兴了:“真不爽快!徒有外表。”
恩人面前咋都从:“成。她们今晚不会再来,已经这钟点儿啦,明儿我再搬过来,还得和录像站老板打个招呼。”
“那不一定,今儿夜我过去陪你。”野青用枕巾把匕首卷好,提在手里。
无奈,就这样吧!再没啥法子。看表,是后半宿三点过。
B面有风,凉快。笔直的街子上湿啦啦,像有谁泼过水。无人,只有呱哒呱哒,木屐声。
路过寺庙时,月牙正向飞檐角尖上滑落。悬乎乎,要跌碎。
我住的小屋,地道的砖瓦房,门窗还大敞着。平日是录像站售票处,夜里给值班员歇脚。两张竹制的单人床,松松懈懈支着蚊帐。没敢开灯,借着月光,我随便用盆里的剩水擦了擦身子,上了床。听见野青插门的动静后,我隔着蚊帐看她脱衣服,脱完上了另一张床。
这么晚了,竟一点儿困意没有。两张嘴巴,在各自的帐子里说起话来。
她说:“你知道吗,我阿爸是中国人,我阿妈是缅甸人。”
“唔,友好邻邦。”
“听我姑姑说,他俩那会儿搞对象可难啦,总得等晚间黑麻下来,偷摸到界碑见面。但面对面谁也不敢过到界碑那边去,只能偶尔拉一下手,又赶紧松开,像中间隔着一座大山。你知道吗,那年头谁要是过了界碑半步,是要被政府枪毙的。这日子他们苦熬了两年,有一天突然阿妈发现怀上我,爸就再不管不顾了,冒死跑过来。跑过来,也不敢在镇上住,东藏西躲。我五岁那年,政府允许了界碑两边通婚,爸才踏踏实实在家住了一年。全家人在一块,日子真幸福。爸只要在,就老抱着我。可福日子短,苦日子长,也就是那年,阿妈得了疟疾去世了。妈不在了,爸一天到晚没魂似的四处乱转。不多久,也跟着马帮走了,把我一人扔在家里。你说,我这命多苦啊。”
“我们能高高兴兴地活着,就不赖。”我觉得她的故事真逗,界碑隔着她爹妈搞对象,谁也不敢过去,可却怀上了她。
她说:“我自小就没心没肺的,心烦事儿不多。”说到这里,她一转话题问:“哎,你说男人女人是怎么回事儿?”
不知道她想知道什么,我就说:“男人女人,是一码子事儿”。
“那,干嘛男人总可以串姑娘,我们就不能串小伙?”
“这是你们祖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和风俗。”
野青问:“你说我是姑娘,我就该有男人来串我,对吧?”
“当然。”
“可男孩子只跟我一块玩,串我的一个没有。”
“男女恋爱是两人的事儿,你对男孩子也可以主动一些。”
“好,我今天主动,我想让你串我,行吗?”
其实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截了当。
“你不想让我上你的床?”
我赶紧说:“粘粘糊糊,热死啦!”
野青更直截了当:“想做爱吗?”
“你这么小岁数,怎么啥都懂?”
“我这岁数,这镇子和附近的寨子,当妈的有的是。男人女人的事都说复杂,其实是最简单不过了,像北面的界碑,过你的就是了。”
我心里琢磨,哦,话说得铿锵有理,这丫头真不简单!
“倒是人们自己,把简单扼要的搞复杂了。这方面的书我读过,这方面的录影带,我也看过。我都懂!”
“懂也是皮毛,你还小!”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这里十四岁就生孩子,相当于你们北京的二十岁大姑娘。我们这里热,在回归线以南。明白嘛,成熟得早。”
“我听明白啦!可我想问你件事儿,不知你知道不知道?”
“说!”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人家,见个小孩。”我很想把话岔开,正好找到话题。
“你说?找谁,这是我的长项。方圆十几里,没有不认识我的,也没有我不认识的。你说。”
“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两岁多不仅会说几种话,还会模仿野猫跳,兔子跑,竹叶翻,蒿杆儿撬。娃娃自己说他不是界碑这边的人,是界碑那边嘎甲寨的。说他……”
野青,抢过话:“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是南坪的,有人叫他小神仙,对吧?!你也不用去找了,那个小男孩走丢了。”
“啊?”我翘起了身,咧开大嘴,半晌儿没合上。
“自从这事情传出来,好多人都去他家看。天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看稀罕,像晴晚间的萤火虫儿似的,一拨拨一串串一团团,小孩子就吓得跑丢了。他妈都急疯了,披头散发不吃不喝。你再去,让她逮着,非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不可。别那么好奇,好奇太过分,会要命的。”
她煞有介事,像个老大姐,但我还是重重地“噢”了一声。又不死心:“但小孩总是得找到。弄清他身上的奇异现象,也许正是解开人类生命秘密的钥匙。”
“奇异,我们这里的奇异,还多呐。”
“说说。”
“就在不久前,录像站的老板陪他老婆回娘家,就是在南坪的竹林里,看到一条十几米长的大蟒蛇,没有尾巴,两头都是脑袋。”
“啊。”我惊呼了一下。
“啊什么,我过去啦?”野青试探着,声音又变成小女孩。
“不行!”说得干脆,我的心里却有了动静。
“我还一次没成功过呢!你年岁正当,人又好,姑娘肯定少不了。你道上道下里里外外有经验,准是个老手,一定行!”
“不成!”我只会说不成,身上燥热难过。
“您越拒绝我,越证明您是个好人,不是个花贼。所以我今天就以身相许给您了,给个好人,总比给个坏人强。我以前有个男朋友,他进不到我里边来,都不跟我好了。毕业时,我的体育老师也鼓捣了一宿,没成,也不跟我好啦。您说,我是不是有病啊?”野青悱恻的声调,哀怨得像在哭。
“别难过,我会跟你好!”我本意是想安慰安慰她,想表达自己很喜欢她,但怕她误会没敢说又怕冷场,急慌中竟然顺嘴溜出这么一句话。正寻思着用什么遮一下,她已经光裸着连个裤头都没穿,钻进了我的帐子。
野青爬到我身上,凉滑滑的。没招儿,我只好打趣:“怎么像条蛇!”说完侧过身,把腿交叉起来。
野青说:“别怕,大哥。你说我是什么都行,说什么我都不会跟你急。是蛇、是鸡、是白虎、是坏女孩,都行。就是别老闪着我,好像我在强奸你,好像我是个没人要的东西。”
“不会的,你还年龄小。”我有些自欺欺人,此时的脑袋里想法单一,一定要控制自己。她说得对,这地方的孩子成熟得早。
“瞎说吧!还是大哥呢?一点也不负责任。你说对了,我就是一条蛇,缠在你身上,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她搂紧我的脖子哭泣,撒起娇。泪水流满了我胸口,滑滑渍渍。
世界上的蹊跷,别都让一个人碰上。其实我有想法,心怀鬼胎憋着没问,这时候实在绷不住劲儿了:“你说的那个中学体育老师,姓什么?”
“姓肖,叫肖吾,怎么啦?”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攒起双腿,把阴暗的旮旯,遮挡严密。
“我不是不知道。我男朋友进不来,是他着急没经验;我们肖老师进不来,是他的蔫头蔫脑不够结实。全在外边哗啦啦了。”她说着话,泪水却没忘记流,哗哗啦啦的。
“您很善良。”她说着,一只手摸到我的东西:“这么结实,真好,像根老甘蔗,快进来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试一试,还让我跪下怎么着。我的膝盖从没给任何人下过跪。我不是坏,我是喜欢你。我看过一个录影带,说处女第一次,一定要跟有经验的成熟男人做,疼痛就会减少好多。来吧,啊……我以后要当姑娘,不当假小子。您就当可怜我,把我成全了吧!求你好好喜欢喜欢我吧,我觉得你是喜欢我的,要不我给你跪下。”她真是个孩子。
“我尝不到甘蔗,怎么知道甜?你让我这么惦记着,惦记到什么时候。还说跟我好,好什么好,好虚伪。”她停下了手,却没离开。
我开始讲大道理,挖空心思。社会伦理,道德情操,做人规范。以及乱七八糟我在路上碰到的怪异事儿。因为不这样,我是难以解决自己的。这叫欲望转移。
野青终究是个孩子,她的头歪斜到竹席上,睡着了。我悄悄下了床,用凉水,擦洗了一阵子。之后,上了另一张床。我长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让胸口的起伏缓冲下来。
枕边野青的内裤和胸罩,散发着一股股女人的味道,刺激着我的每一根儿神经。鬼使神差地又涌起跃跃欲试的想法,一种想看看她的冲动。刚才她的一切,我似乎都想不起来了。顺便再给她穿上裤衩。我果真虚伪地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一个台阶。其实不尽然,其实我是想:过了这村,往后就没了这店了。
我拿起她的手电筒,下了床,连鞋子都没穿,蹑手蹑脚走过去。每一步,我都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努力。我觉得自个儿很可笑,似乎迈出的每一脚,都跨过一座大山,超越了一个峰巅,铅坠一样的沉重。怪了,不就这点儿鸡巴事吗,怎么这么折腾人。在大漠徒步,在雪域跋涉,与歹徒周旋,和狗熊赛跑,一切的一切,都没如此不堪负荷。今儿一个小姑娘,居然把我整治得魂不守舍,飘飘然。
撂开蚊帐,她还是侧躺着。我把她轻轻搬起放平,曲着的腿拉直,像个“大”字。手电的光束,躲避着她的脸,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忍耐着那家伙在身体中部的跳跃,全身心观赏着这件精美的天然造化。
我终于放下蚊帐,倒退着,用手电筒敲击着自己的脑壳,然后叼住电筒。面对着墙角,闭上了眼睛……我兴奋起来,没头没脑地解决了自己。
...............
《山花》年第8期目录
小说苑
陈鹏→斑马(中篇)
陈鹏→灾难之下,岂有“完人”
(创作谈)
曾哲→不折不扣之阿瓦山歌·野青
李月峰→不过如此(中篇)
洪琛→有关储藏室及其它
开端季
李黎→午夜的安东尼
散文随笔
于是→光芒只照亮他的鼻尖
刘汀→乡村小学
诗与思
东君→东君的诗(十三首)
东君→形式之内,形式之外
诗人自选
谷禾→一样的月光(外八首)
桑子→神在细小的事物中(外一首)
大视野
张颐武徐勇崔柯夏烈→
“文学类型与类型文学”笔谈(一)
易彬→诗学随笔(二则)
视觉人文
陈敏→不羁的乡村画家
企业论坛
茅台“十三五”规划解读系
娌荤枟鐧界櫆椋庡幓鍝噷濂?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庡摢瀹跺尰闄㈡潈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