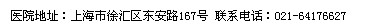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护理 > 生命曾经难以承受之轻
生命曾经难以承受之轻
刚闻大宾走了,我心里一沉。伤感之后默默地计数,所知的这是第13个。云南建设兵团七团四营十三连当时是个新建知青连,只70多人,成都知青占62人。我们返城后各忙生计,难得一见,但隔年都有噩耗传闻,天知道不是当年的晦运作崇?在如今高龄多见的社会里,知青战友从20岁到50多岁,就先后离世。我这个当年的重病号侥幸存活至今,只有一声叹息。
唯有叹息而已,这是感悟到生命代价之沉重的叹息。
(▲后右一是去逝的兴凤)
“人命关天”、珍视生命,说来是人的本能感知,可知青却缺乏这人生起码的感悟。那年头动不动就是“为上山下乡奉献青春”、“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甘献生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出生以来,只吸吮这特制配方奶生长,理所当然地把生命价值的第一要义当作“牺牲”、“奉献”,个体差异只在于中毒的深浅不同,或虔诚或被动罢了。那个年代,一切以主义、国家、集体为重,个体生命的分量微不足道,生命不可思议地轻,更何况少年轻狂的我们。
当学生时,“誓死”“献身”……不厌其烦地表决心,仅限于纸上谈兵,踏上南疆土地的第一个月,开始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份量之轻,死神完全不在乎“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燃烧呢还是泯灭。
在上山开荒种胶之初,我连先是协助南定河边的四营四连,在沼泽地恳荒,除每天与泥沼中的蚂蟥、蛇、蟒、蚊紧涨地大战之外,日日还要穿行于芦草无边的沼泽泥潭。其中段段险途必须人随人脚跟脚战战兢兢地踩着独木、草根、泥潭,一寸寸挪过去移回来。咒骂声,惊叫声,呜咽声都只有在敛声迸气涉过各段险途后才暴发出来。
那天清晨,薄雾蒙蒙,我们女生8班一行打头踏上出工路,我断后。刚进沼泽就是必经的10米左右的独木桥,圆滾滾的独木略高于水面,水草清浅可见。我一踏上桥面发现朝露把脚下的木头浸润得湿漉漉的,好滑,连连叫“小心!”刚落音,前面“扑咚”一声,埋头蛇行的女生都吓傻了,一看是和我相隔一人的雪红掉下去了。脚下的清水瞬间涌起团团污黑的泥浆却不见人影。我的血往头上冲,手脚却不知所措,其它人也都呆若木鸡。突然污水中两只黑棍突刺而出在空中乱舞,大家这才醒过神来。我和邻近的同伴拽紧这双黑棍般冰凉的的手,稳住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把雪红拖上来,几乎是爬行回到岸边。
可怜能歌善舞的校花雪红哦,全身上下还有满脸都像被墨染过,只有两只大眼白愣愣地,好像魂还没附体,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最可怕的是满头满脸的乱发根上缀的不仅是腐草污泥,大大小小的蚂蝗紧附其上荡悠着。谁也顾不上说什么,都七手八脚地朝雪红泼水冲洗。事后越想越怕:差点就——就那么轻易地走了,值吗?
(▲在沼泽地里种甘蔗的我班部分人,左一的大宾和左四的宏秀均已逝、左二是雪红、右三是作者。)
因不放心发烧躺在茅屋的同伴,我曾利用中午吃饭时间,独自一人多次往返于这条危机四伏的沼泽小道,每次小心地提着锄头探路,脑子里禁不住这个念头:我会被无边的泥泞静静地吞没吗?值吗?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这个可能呀!我很侥幸,多少年后,还有机会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看到送信的女兵陷入沼泽的没顶之灾时,我的眼泪加倍地涌出。
付出生命的可能不久就成了事实。
我们这个70多人的新建连队,进山两年,砍了周边连绵山头的原始森林,开带挖穴种下多亩橡胶苗和上百亩玉米。高强度压力考验着稚弱的身体和精神,尤其是雨季的疟疾高发期。一般发病者就在卫生员手上吃几颗药,几天不出工,烧退就算了事。副连长老沈发虐疾时,烧得温度表都超计了,水米不进昏睡几天,活过来又带队上山了。排长阿容发烧,人昏迷不醒,知青们砍青竹绑个担架抬下山去营部卫生院医治,捞了一条命回来。关键还不止受此一次磨难,只要沾上这病,几乎年年发作,回想起来苦不堪言,当年却以为这一切都是生命本该承受的。我连90%的人都得过疟疾,也都是这么拖过来的。男生杨庭华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年雨季。杨病了好些天,不仅高烧,还叫头痛。大雨小雨下个不停,大路冲垮、小路泡在烂泥里,拖拉机肯定是上不来,抬着走吧,脚都没下处,怎么下山?拖吧,说不定睡一觉就好些了呢?天黑得早,煤油又珍贵,大家都早上床早歇息。夜里,周围山林啸声阵阵,身边屋檐雨脚不停。半梦半醒的,一声凄厉的惨叫,盖过所有的风声雨声,全连人从梦中惊醒。疟原虫向杨庭华脑部侵入,让他头如刀剜,一阵阵一声声哀嚎不绝。天刚亮,大家扎起了担架,迎着暴雨往山下走。排长高峰等4个扶担架的人双脚在泥泞中探路,另4个抬担架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背走。这么一路扯扯跘跘地挨过了10多里山路,把昏昏糊糊的杨医院。一声“不行了,要输血!”吓得同伴返身又上山报信。等全连战友得知消息,不顾一切跑下山,天已快黑了。一条条胳膊伸出来,等着验血输血,可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一些跑得上气接不到下气,落在后面的人,都没等到再看一眼,杨庭华已没力气呻吟吼叫了,活活痛死的。
回想起在山上烧荒时偶现桂圆树、橄榄树、老梨树。老员工说那是早年叫不出族名的山民所居山寨。因瘟疫肆掠,家家死人不断,有些甚至全寨族人灭绝,为逃避死神不得不焚寨搬迁。闻此言,好庆幸有了现代医学成果——喹啉丸,以为我们虽遭受病痛而不至于送命了吧,没想到还是有这一天。
当杨庭华的亲人闻讯,千里迢迢从成都赶来时,炎热发臭的尸体早就埋在橡胶林下了。现在想起来,最不近人情的是,身为战友,甚至父母都没能痛痛快快哭一场。当时,所有的人心里都苦,却又时时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最高指示罩着,何况谁也没认定这是光荣牺牲啊。好意思拼命嚷嚷吗?那时,生命的份量是如此这般之轻,哪怕是不到20岁的生命。
男生李荣华的死更是静悄悄的,他什么时候得的病,去世时谁在身旁,说了什么,大家都不能确定。只医院一段时间后,传来消息,说是得肝腹水死了。这医院前肚子就大了,累得很。老连长当时还推着他上山,说累点算啥,你是连队里首批的共青团员,坚持坚持。听说他挖橡胶穴时弯不下腰只有跪着挖。他孤零零地死在远离连医院,离成都家乡也有万里之程,也没听说谁参加他了的葬礼。刚过20岁的生命轻轻地、轻轻地飘然而去。
胶林旁的另一场“葬礼”更是让人不堪回首。年吧,先是入边境的军马瘁死,然后狗吃马肉得病,再后来是人吃狗肉得病,我营七连的一家老小、还有另一家人连续病死。北京来人了,说是炭疽病,属二号传染病。全身披卦防毒面具的医务人员把死人、死狗、死马捆绑在一起泼上汽油,架上柴堆,烧了好久好久。然后深埋,然后发禁令:各连队人员不得相互联系,山上人员不准下山。
这道禁令在知青中引起的恐慌比炭疽病本身还大。知青远离家乡在边境深山,就靠着邮件和亲人一线相连,不能下山取信,等于断了那根要命的线,还有那些和马、狗熔为一体的人影时不时闪现在眼前,人畜同命,同化为轻烟……那是一段令人窒息的煎熬期。
疫情险境几个月终于过去了,生命的贵重、人格的尊严、生存的权利等等意识离我们更远更淡了。以至后来,哪怕是面临死神,都不是害怕死亡,而是遗憾没有更多的贡献(牺牲)。
年初的一个傍晚,我自感不适早早地上床休息,哪知心臓越来越不对劲,按捺不住地蹦蹦急跳,要跳出嗓子眼了。同屋的小波见我气喘得苦,忙叫来卫生员丁占红。丁沉着地摸脉博,手一搭上就慌了,忙回医务室拿了强心针来,颤抖的手稳了又稳也没扎到我身上。我觉得呼吸困难,舌头发麻,说不出话,手脚痉挛,以为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心中并不害怕,只是遗憾:刚满24岁才几天,什么(关于主义的大事)都没做呀……爸妈心里会多疼,不能想这个,更喘不上气,听命吧……针刚扎到身上,突然暴发性地呕吐,喷得围拢的卫生员、小波、亚平那个狼狈相呀。袭向头部的麻感消退了,发硬的舌关有了知觉,喘息竟轻松了不少,心跳开始一波比一波缓下来,又闯过一次鬼门关。
就这种日子,还有人羡慕。
一个上海女知青连长和老沈开会住一屋,深夜交心,得知老沈没耍男友、要独善其身后羡慕不已,一声叹息“好幸福啊!”当时,老沈还不得其解。几个月后,营部发文,撤消那个女连长的职务。随后,得知她回沪探亲不获批,肚里孩子一天天见大,但因不交待为父的一方而不让其及早引产。待产前二个月时,剜心掏肺般惨叫声中孩子被钳出,并活埋了。土浅,啼哭声传出,有人不忍,又挖出,又埋。终于,男方——一个成都男知青不堪承受上吊自杀。
与此相比,我等所遭之罪真的不算啥了。
年初和初年,我和小波等人两次被长枪短轮在眼前晃动威逼,“交出总理遗言”“交出江青谣言”。我拒绝在审查记录上签字,被全连大会批斗,并扬言将解押关禁并轮转到各连队批斗。
从来不懂珍爱自己的我们,本想把一腔热血洒向胶林,把壮丽青春献给边疆,换来的却是身心俱残和一次次清查、批斗,倍觉冤屈?那知比我们更冤者还有。我团二营的一个成都知青,从不关心政要大事,只因接待了另一个被怀疑的知青,就在清查审讯时被逼自杀。相比而言不能不承认,我们可算是侥幸地受到命运之神的光顾。也许是自已还没对生命轻贱到如此地步,也许是老教导员暗暗保护的作用。
璨如春花的生命在蛮荒野岭间默默地煙灭,轻飘飘的消失,烟雾一样散去。那时,人人都要背诵:“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谁去掂过这些逝去生命的份量呢?
最后离开“梦游”8年的南疆深山,也是靠知青豁出命误打误撞闹成气的。年开始,云南支边知青要求返城,抬尸游行、罢工、上京请愿、铁道卧轨,无一不是以命相博。云南农场此起彼伏的知青呐喊声在孟定达到高潮。(▲正罢工的知青和面对知青的赵凡——照片引自《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
年1月6日,我团四川知青在孟定坝发起绝食抗争,不达到目的绝不进食。条男女汉子自行封闭于七团团部一小院,连水都不喝一口,以示决绝之志。第二天就出现有人昏厥的现象,一群20几岁的鲜活生命眼见奄奄一息。赵凡(赶到现场的中央调查团长)对死心踏地的绝食者和外围几千或跪或泣的知青说话了“知青同志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与此同时,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长的声援,境外电台的争相报道,中越边境一触即发的军情都起了发酵作用。直达北京的热线电话那头,听汇报的一群大佬中,时任四川老大的紫阳最先表态:可以安置我省的支边知青,各省老大随逐一附议赞同。自此,绝食知青中昏迷不醒的医院救助,知青的生命被正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恶运也自此终结。被轻视并自轻的我们也开始重新掂量生命的价值。
16岁时,我立志“誓死扎根边疆,建设边疆”,20岁时,我说过“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一次次与死神插肩而过,一个个被掠夺的生命也没能惊醒梦中人。乌托邦,就是一副只对虔诚者下的毒药,这副药我和虔诚的朋友从小就喝着它长大,岂是三年五载能解脱的。尽管我们始终在寻路,学习着思考,但我和大多数沉梦中的人都不是顾准、李昭、遇罗克、张志新,只有历史发展的事实才能唤醒中毒的梦中人。
我想起一次无知无畏直奔终点的亡命之举,倒像是8年知青奋斗生活的缩影。
我那窝在深山里的连队,依赖了一年多的煤油灯后,终于下决心从坝子引电上山。大约有电站的人指导,另外除几个老职工外,就是我们几十个一点不懂行的知青。山路遥远,听不见指挥,电缆向前就是使劲冲锋的号令。个个摩拳擦掌,按分工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地沿起始线路站着。想着在可电灯下看书,能不摸黑进茅坑,个个劲头十足。
刚起步时,还能相互喊话打手势加油,随着线路向山上沿伸,组与组分散了,后来连每个人之间的距离也长得不见踪影,只有手中的电缆时不时向前方移动。电缆线是直通山上的,我的脚下却没有直路,一会儿在丛林中乱窜;一会儿在岩边穿梭;一会儿一点没动静,干晒太阳喂蚂蚁;一会儿随电缆在阵雨中猛跑,累得半死。终于觉得顺畅了,大踏步紧拽着电缆向上攀援。说实话还真分不清是我在拉电线还是电线在拉我。突然脚下路断了,浑黄湍急的河水令人目眩,脑子里空空的,拼命地攥死抖动向前的电缆,忽高忽低吊甩甩地跃过急流才长出一口气来。现在也记不得是怎么回到连队的山窝窝中,记忆被吓得中断,定格在那浑浊的急流中。当然,电线送上去了,电灯也亮了。可这事办得糊涂又惊险,真不知我那份力用上了吗?手一松,小命拣得起来吗?一瞬间的事而已。
这糊涂又自信之举,不就是支边云南8年的缩影?直奔着建边疆种橡胶的目标而去,对国体动荡、农场基础、自身实力、边界复杂等现实全然无知。像一股清风妄图穿透波繘云诡之迷雾,无知无畏地横冲直撞,岂有不烟消云散之理,岂能不付出惨痛代价。
唯一可珍惜的是,这一切我们都承受过来了,今天的价值观、包容量、淡然和理智都是从青春代价的基石上成长起来的。
历史的进程中,知青曾经是试错的棋子,生存在进退举手之间,生命的份量曾经如此不堪承受之轻。但只有如此的生命体验,才确知社会的进步是随着每一个体生命的增值而实现的。
哪里看白癜风专业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哪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