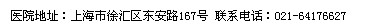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疟疾 > 疟疾病因 > 饶毅王鸿飞在西湖大学的对话完整版把
饶毅王鸿飞在西湖大学的对话完整版把
ios开发求职招聘微信群 http://www.bcutexas.net/chaoliu/xinchao/1608.html本文转自饶议科学-11-24文章《在西湖大学的对话(完整版):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做美妙的科学》。前言:今天推文比较长,是未删减版。主题:西湖大学校董面对面时间:年10月11日7:30--9:50地点:西湖大学5号楼1F主讲:饶毅、王鸿飞第一部分长视频(知识分子)《关于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王鸿飞: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面对面的WeMeet活动。和饶毅认识有十几年了,经常有人把他和我的第一个学生混淆,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名字跟他一模一样。很多人经常跟我讲说,你真厉害,饶毅都是你的学生,我说是另外一个饶毅。我那个学生现在在美国一个学校做faculty,他是我在北京时学生,你们以前应该是亲戚,他们家以前也是江西的。饶毅:我介绍一下王鸿飞老师。王鸿飞老师跟我年龄是有一点差别,比我年纪稍微小一点,但基本上是一代。这一代的特征就是学化学的是看不起学生物的,他一直认为我做的生物就是看果蝇怎么打架,怎么交配,没有什么科学,他一直称我们的科学是软科学。王鸿飞:我有吗?饶毅:在私下的时候。他是科大化学系毕业的,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挺厉害的学校,学了化学。回国来,他觉得他的化学特别厉害,后面半句话,我就删掉了,帮你不得罪人了哈。他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先从中国去了美国,在西北国家实验室做教授。西北国家实验室是以前谢晓亮在那边做过教授的,后来有王鸿飞,所以他非常高的一个人,西湖大学的学生以后听他的课,千万要问清楚他是怎么打分的。要不然你得很低分时,不知道搞错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给你这么低的分!王鸿飞:所以他讲的都是谣言哈。我们今天主要想讨论的东西,我想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科学;第二个,什么是好的大学。反过来讲,也许我们反过来问可能更好一点,我们西湖应该做什么样的科学,我们西湖应该做什么样的大学,这是我们想围绕讨论的主题。一开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关于科学的事情。--------------------第1个短视频(赛先生):《讨论诺贝尔奖,关中国人什么事?》我们都知道饶毅喜欢预测谁能得诺贝尔奖,谁不能得诺贝尔奖。而且有时候据说还预测的比较准。我是一般从来不预测的,因为我觉得谁得都可以,只要是我认识的人我就很高兴。我要不认识的人,我就觉得反正我也不认识,也不会高兴。饶毅:我认为讨论诺贝尔奖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任何行业都有对工作做得好和不好的判断。判断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通过发表评论,实际上是可以互相影响的行为。诺贝尔奖在多年来,是全世界自然科学方面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而且对于推动科学,对于我们很多人做科学有清晰的影响、不可否定的影响。讨论诺贝尔奖金本身不是像有些人假扮“不关心”。你如果不是科学家,可以不关心,关心了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就像说谁的企业做得好不好,谁的文学写得好不好,我可能也不关心,因为我关心了也搞不懂。不懂的时候不关心,不算事情,但在同行业里和相近的行业里关心是自然的。当然还有一大批人很虚伪,首先虚伪的是有一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得了奖之后说,“哎呀,这不是我所关心的”。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没被任何人所拒绝,包括爱因斯坦同志,所以任何人说我得了奖不关心的人,这句话93.7%的可能性是说假话。你既然不关心,你就不要它,不要做诺贝尔奖的winner,你应该做诺贝尔奖的loser。虚伪的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明明为这个奖去斯德哥尔摩很多次,甚至某一年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希望影响结局。然后拿了之后,他说不关心。还有一部分人跟诺贝尔奖金差的很远,然后也假装不在乎一样,这是说没有意义的假话,我们不关心这类假话。不是说关心诺奖,就天天哭爹叫娘,觉得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讨论它,实际上在讨论科学的进展,讨论科学到什么时候做到什么程度,然后还包括科学的品位。科学的进展,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科学往前走了多少,对本学科或更大的科学领域、以及人类社会产生了多少影响,这是科学的判断。除了这一部分之外,那还有科学的方式、风格和品位。风格和品位,在实验科学方面,生物、化学,风格和品位也讲究,但讲究的比较低。讲究高的是物理学,物理学在它的光辉灿烂时代,也就是年前的物理学,人家觉得不光要重要,发现E=MC2,或者发现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还要做得很深刻、很优雅,elegant。物理学的人还踩化学,会问得诺贝尔奖是物理的、还是化学的,化学就是比较差一点。因为王鸿飞在私下踩生物踩了很多,所以我今天也开玩笑用物理来踩化学。王鸿飞:刚才大家已经说过了,我是物理学会的会事,我不知道他在踩谁,而且诺贝尔奖本来就是学化学的人发的。8:00王鸿飞:你对今年的诺贝尔奖有什么具体的评价没有?饶毅:今年的奖,你们学物理、化学的不懂,生物里人人都知道这个工作会得奖,而且一大部分实验室都在天天用这个技术,所以这个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奖很难发,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常用的三种技术(前面两种是Zincfinger,TALEN),CRISPR-Cas9是第三种。第三种的起源就是很长时间以前,有西班牙科学家,日本科学家,在做很多人不重视的,很小的领域做,做了很久的一般性研究,到了一定时候,才突然有人意识到这可以应用,所以前面就一串铺垫,你也可以故意把奖给那几个人,这也是一种给法。如果给EmmanuelleCharpentier和JenniferA.Doudna,她们两个人和立陶宛的科学家同时做出来的,立陶宛的科学家稿子寄给杂志时,被拒稿,好像发表时比她们晚,实际上差不多时间。后面再有其他人赶快贴上来,往后扩展,也是重要的工作。但是像我这种人,或者像你这种人就会挑剔,这是扩展性工作,那就不得奖,但也很重要。除了这个工作之外,另外锌指核酸酶(ZFNs),转录激活样效应因子核酸酶(TALEN)那两个技术也是可以用的,而且那两个技术开始打破这个长期技术没有进展,所以这个奖有很多给的方法。中国人关心的是华人得不得奖。我认为我们张锋同学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总觉得要再好一点就更好。而且我的角度不是像有些人批评人,是很痛苦和很妒忌,我不高兴时常常是因为我失望了,因为我对人间的期待特别高,对他们。张锋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从中国出去,在那边长大,他可能九岁、十岁才去的,然后在哈佛读的本科,斯坦福读的Ph.D.,MIT、哈佛拿的教职,所以他是金灿灿的一条路,所以就要走得漂亮。在一定程度上,我虽然不认识他父母,我相信他父母跟我们是差不多时代去美国,可能年龄会比我们稍微大一点,我很希望这些人的孩子得诺贝尔奖。但我会希望高一点,你这么聪明,这么好的路,就应该走得漂亮。有一个背景,我比较早知道他,是在年之前知道他,他的实验室有一个学生以前是我实验室的学生。我知道这个学生去以前在想什么事情,他就在想做TALEN。张锋是MITMcGovern脑研究所的研究员,我是北大脑研究所的,我们以前每两年开一次会。年左右,他跟MITMcGovern到北大来开学术报告会,MIT有几个人讲,北大有几个人讲,清华有几个人讲,北师大有几个人讲。他当时在做TALEN,我就笑起来了,我说北大都有学生在做TALEN,你在MIT还做TALEN,我说你爹妈要知道了,会觉得你白去美国了,我说你得往前走一下。另外,他自己研究生时期的工作也很出名,做光遗传学,光遗传学很明确,是EdwardBoyden和KarlDeisseroth,他们做了以后,张峰加入他(KarlDeisseroth)的实验室,所以是跟着他们做的。我说你上次很出名是跟着别人做,这次不要又跟别人做,所以当他CRISPR-Cas9第三次跟别人做时,我心里就觉得他肯定根本不记得我讲过这一点。可是我的学生记得,我在前几天时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说当时怎么发生的,他说知道,他现在在国外,他说我当时特别不讲理,拖着他去找张锋说,这个不能做。这学生认为人家做什么,关你什么事情。是不关心我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爹妈带他出国,他也读了哈佛、斯坦福,又在MIT工作,我就希望他做得特别好,对我来说有点失望,而不是其他原因。我是希望他做得更好,你孩子以后没得诺贝尔奖,肯定我也是这样说。王鸿飞:那么这次诺贝尔奖,你觉得是技术上的发展,还是其他的?饶毅:当然是纯技术,因为也没有给人家前面那些科学诺奖,给的是做技术的,但这个技术太重要了。基因修饰,原来就有可以做的方法,在老鼠、果蝇里能做。CRISPR-Cas9出来之后,是鸡鸭猫狗都能用,这“鸡鸭猫狗”是指研究工作者。能用的地方,也是不管鸡鸭猫狗,也是都能工作,这个技术特别强大。其实我们更关心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在中国能够开展这样的工作。你讲到有taste,在有些很多方面,又跟我们的技术有关系。你讲到不要去跟风,其实我有时候的感觉,我们很多工作是跟的不够快,而不是不跟。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是在跟着几十年前的东西,自己还在那儿琢磨别人早做过的东西。饶毅:你是哪一年回国的,第一次回国是哪一年?王鸿飞:第一次回国99年。饶毅:所以你带着古老时期的想法,在年代之前,中国跟世界的东西,是跟得比较慢。现在不是,现在中国东西是跟得特快,所有科学在一定程度都是跟,没几个人在现代做科学是从0开始,只是说跟别人有多远,推动有多远。跟别人做没有什么错。你可以跟的更好,在原有基础上做得更好,这没有问题。我反对的是“紧密追踪型”。追踪到别人还没有发表,你已经偷听到了,就开始做了。或者别人刚发表,你就开始紧接着别人后面做,这是合理合法的,只是不Elegant。杭州离上海比较近,在上海话里面这叫“吃相难看”。现在与99年差别很大,现在大量的华人和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但凡国外已有了,我们都会,都接得很快。这时,我们再谈接得快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一种style,这种style就是说我们在穷的时候,很差劲的时候能够学就不错了。疫苗、抗生素,我们在三四十年代国外发明之后,我们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慢慢也能生产,这很值得,没有好的疫苗、没有好的抗生素,一半人就死掉了,爹妈都不存在。这种跟得越快越好,这是有意义的。但是等到我们科学训练基础普遍很好了,等到我们研究条件普遍很好了,不仅西湖大学的研究条件好,中国一大堆地方,王鸿飞以前待过的国内单位研究条件都很好,特别经费都特别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退一下想:还要有一小部分人是做又重要,又深刻,又优雅的科学。这时候才有条件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老是要跟着别人汗味后面,看出多少汗可以跑过别人。王鸿飞:那你觉得我们是培养能够有这样眼光的人好呢,还是改变一些本来没有眼光的人,让他们变得有眼光呢?饶毅:我觉得第二点(改变眼光)是做不到的,所以是培养。我不仅是这样说的,而是这样做的。我从年开始在科学院和北大清华,我还在美国期间上课,我就讲孟德尔,因为孟德尔在生物里很特别,孟德尔做重要、深刻、优雅的科学。而且他的文章非常漂亮。我这里有一个对达尔文不尊重,达尔文工作都做得很好,达尔文的书和论文像写文学作品一样。同时代的孟德尔写的论文很像我们现在写的论文,所以我比较偏好孟德尔。我在07年全职回北大之后,从08年开始,我开一门课,这门课现在名字叫做《生物学概念与途径》,我自己讲一部分,然后我请施一公、王晓东、谢晓亮他们分别讲一堂课,这个课程我是写了一本书,我计划写12章,我写了11章,在实验室网站上谁都可以去看。我修改之后,修改版发上去,我这里挑的是生物学的,我认为既重要又深刻,还优雅的科学,所以西湖大学应该率先在北大之外的全国使用我这课本。王鸿飞:其实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我们西湖面临着招什么样的人,和鼓励他们做什么样科学的任务。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讲到下面一个话题,我们要办什么样的大学。你刚才讲了什么样的科学是好的,什么样taste是好的,我们怎么样找到这样的人,或者培养到这样的人,或者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研究。作为校董和校长和研究人员,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谈这个事情。饶毅:我觉得西湖大学是我们国家现在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大学,国家给予非常好的支持。浙江、杭州和西湖区,我都知道,他们都给了非常好的支持,全方位的给支持。等我们西湖现在的同学毕业了之后,再过30年,那个时候你们再写现在的历史,你才发现你在校期间居然不知道有很多历史,会很有趣。要做好这个工作,肯定学校本身结构要做好。同时,要在国家重视自然科学和工程的环境下,才有这种可能。在社会环境不具备的情况下,这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另外,学校,从它的治理结构和它请到的老师是什么人,关系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鸿飞,他年纪不大,地方走了很远。王鸿飞:我也50多岁了。饶毅:永无休止的人,他在挑剔别人,经常对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在底下一天到晚批我,把我批的臭死。王鸿飞:他今天在报复我。饶毅:我这个人是比较nice的一个人,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有多nice。别人叫他来主持,我也就吞下去了,就主持吧。王鸿飞:可能我有时候批你时,又把你当成我学生了。饶毅:他在过去三个星期之内,把我批的体无完肤,所以我觉得西湖有这样的老师,肯定学校看中了他,不是他挑剔,而是他对科学确实有很好的追求,对科学的品位有很好的追求,而且很愿意教学生,那么有这些特质,是请他来西湖大学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只会骂我,就叫他来了,这个不能算标准,至少不能算主要标准。我一直在看西湖大学招的老师水平和老师的风格,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学校对老师的要求,也是希望他们把研究做好。我觉得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学校,有些华人不懂,认为施一公老师发文章发的多,就认为他主张大家天天赶快发文章。一公不仅在西湖不是这样主张,在清华也不是这样主张。清华有人发文章很少,他对他们非常支持。有些发文章发的多的,他不一定那么支持。所以大家清楚的知道,一公有一公的特长,他没有要求其他人和其他学科在发文章上跟他一样,他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因为我和他参加过很多共同评审,我可以非常清晰的这样跟大家说。我也希望年轻的老师不要紧张,吓的要死,说一定要跟施一公老师一样,发多少篇Nature,我才能拿Tenure,他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你看看清华生物系,不是这样要求的,你也看看清华生物系有发了Nature而没有拿到Tenure的,仔细看清楚一下。我觉得一公对科学的要求也是挺好的,我们有一批招来的老师。许田老师今天说感冒了,他一天到晚要拖我来辩论。现在我真来了,他就不来了!他对遗传学理解是非常深的,他在复旦读的本科。他跟我是同一年的人。然后邓力老师,化学系的,我也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和王鸿飞大吵过一段,他说我怎么懂谁做的物理好,谁做的数学好。我告诉他,我碰到不同学科的人,我希望了解数学谁好,我会问田刚、夏志宏等,也问问跟他们远一点的数学家。化学我也问过,有人给我开过一个单子,全世界华人有机化学做得最好的十个人,里面就有邓力。所以他一来我就知道,他在我的单子上。我需要这样来了解一些学科的情况,我听不同的人,他们水平都得高,而且品位也有要求,如果都听品位很差的人的意见,我的品位也会差。王鸿飞: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有了条件,有了更好的支持,就能做更好的研究。我不知道像西湖的话,当然我们现在是给大家提供相当好的条件,你对这个条件怎么看?我在这之前可以说一句,我的博士导师从来都是跟我讲,他说看见太多的年轻人被太多的经费所毁掉,因为他们钱太多,所以他们做不好science,不知道你怎么看的?饶毅: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说俏皮话,但我相信要到了一定条件以上才能说这句话。因为你没有在中国读过研究生,我年到年在中国读过研究生,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条件比现在差的太远了,我现在会和学生说,移液器的枪头在-85年中国是没有的,制造不出来的。年到95年,还制造不出来。年时,还制造不出来。因为这是高精尖的仪器,虽然很便宜,里面的物理和化学都要足够好才能很准确的移液,实验才能用。中国在年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接上现代科学实在是相当困难。在这个情况下,不能说年的时候用年仪器就足够做了,这是笑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行的,偶尔可以。但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学校都有足够好的仪器条件情况下,这时候我们就更讲究要做重要的科学。重要的科学对本学科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很清晰的。那么我们做重要的时候,要有原创的发现,那么原创主要是跟同一学科、同一条线,原来差多远。孟德尔这样,在他之前就没有遗传学,他之后遗传学才出来,这当然是很特别的情况。我的老师有一个说法,说所谓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三流科学家,一流就是两个人,牛顿和爱因斯坦;二流就是开创一个学科的人;三流就是得诺贝尔奖的人。他孩子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学老师问他孩子,你爹是什么,他说他爹希望做三流科学家。后来他们赶快开家长会,在美国都是吹大牛的,你儿子是不是心里有毛病,说你要做三流科学家。后面,这个领域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事情,一下子推动很多,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很重要。另外,对于科学发现,这是我主要兴趣。我认为做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很难做,因为科学发现,鸡鸭猫狗发现一点东西都是发现,技术是你要拿下来,最后很多人用的只有一个,其他都不算的,就是用的那个算,其他都忘掉了,所以技术很难做。技术在目前要比以前好做的原因,是因为出版了一个杂志叫NatureMethod。以前生物学的技术一般是在一个研究里说它发明了一个技术,很少是单纯以技术发表文章,很少人愿意发表文章专门做技术,所以影响了技术的发展。Nature、CELL这些杂志,出了一大堆杂志,出版商为了赚钱出的杂志。但它出的技术性杂志,对于生物,现在做技术的人多了很多,跟一个杂志可以出版关系很大。在科学和技术里面,都有可能做很好的工作。王鸿飞:其实我有亲身的体验,我在99年回大陆,回北京做研究时,那时候我们要买一些基本的光学元件和基件都是买不到的。我曾经还专门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做成什么样子。那时候刚开始有一些公司开始做这个事情。在去年我还看到一家公司居然被川普列成他们要惩罚的一个公司,实际上他们是99年才开始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列上去。我的感觉是中国在技术上面,尤其是在实验技术上面,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进步非常的大。现在的研究条件,很多地方的实验室已经比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要好得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饶毅:这时候就不希望普遍继续紧跟人的做法,特别是生命科学,据说物理学现在能做的问题不太多,所以大家都嗡在一起。化学,我就不评论了,你更懂,你不在这里,我肯定要说了。生命科学是遍地有问题,所有凡夫俗子都知道生物学的问题,所以很容易铺开来。但关键是怎么样找到一个自己能做得更深、更远、更优雅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挺重要。我自己是著名的发不出文章来的人,我这十几年回国经常被人讽刺讥笑挖苦,只有少数人知道如果要追求文章,我也能发,只是现在不热衷。我觉得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去专门探索和创造做好的科学的可能性,因为我有一个好处,没人能够逼我做什么东西,我反正有Tenure了。我曾经差一点去德国马普研究所做所长。如果人家给我职位,我去做的话,它的经费是一年万美金,然后7年评审一次,这是做所长。评审如果过了,照样。如果没过,经费削减25%,14年之后再评审。再没过,再削减25%。所以在经历这个过程时,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以前觉得马普所多好,我现在发现其实也伴随很大的问题,你如果去做所长,做的工作还得不到诺贝尔奖,你十足证明自己蠢驴一个,因为什么条件都有。德国还有一个更好条件,德国除了招研究生之外,它的技术人员是专门训练出来,专门做技术,所以做科学的条件非常好。心里最担心的,自己证明自己也是个蠢驴,有自由的时候、有条件的时候做不出重要的东西来,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到底做什么。王鸿飞:是好驴坏驴,我们就走着瞧!饶毅:是的。我还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自己本人做实验不太好,带来实验室缺陷,技术不是特长。别人会做,我也会做。别人不会做,我也不会做。稍微难一点的实验我都不会做,分子生物学技术特别容易做,你们做化学不知道。分子生物学之所以在生物里用的好,DNA是很不容易降解的,鸡鸭猫狗都会做,我也会做。听着又好听,分子生物学。实际上是生物化学难做,蛋白质和RNA降解的很快,就不好做。王鸿飞: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生物化学是化学还是生物?饶毅:我花了很长时间,专门想,先想清楚哪些东西我认为重要。同时,我也想为了做重要的问题,需要什么技术。第三,我一定要派学生去学需要的技术,我学不会,学生学得会。这个事情听过去是很容易的,做起来是很难的。生物化学,我认为它的本质是生物学的问题,用化学的技术。传统的生物化学,本身就是化学的问题,就是糖的代谢、脂的合成,这些都得了诺贝尔奖,也都重要。但对生物学来说,那种东西是过去的老古董,不是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物学是以生物学为导向,用化学技术。生物化学目前是这样,以前是化学,生物里的化学,现在是生物里用化学技术占了很大一块。所以我就想到了几个东西要做,但这几个要用生物化学做,我实验室哪里会做生物化学呢?我自己就不会做。蛋白质的胶,一块都没有跑过。DNA的,我跑过很多。我就在想怎么办,我想某某某,这都是具体有人名的,生物化学都做得很好,他们都不做了,我说真蠢,我就要做。我派人去学,有几种学法,其中北大有一个叫方敏,他是王晓东博士后,他的生化做得很好,他教了一些学生把技术学会了。他自己却回美国了,他的实验室鸟兽散,他把最好的学生送给王晓东,次一批送给我,再差的就送给别人。所以我收了三个留守生。一个过了三个月就走了,另一个很快也毕业了,还剩一个。我发现他确实生物化学好,这时候我设计用生物化学技术的课题,开做了。另外还有一个课题,我觉得也是要用生物化学的方法。老师除了判断方向,还要判断质量,实验室有新技术后,出现困难的时候,我难以判断因学生技术太差了,还是因为我设计错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建立实验室标准,有很大的困惑。困惑的方式就是经常找他们:没有做好没有做好,我们重做,就做好多遍。有一天我意识到不对,其实他们实验做好了,等到我意识到实验室过关了之后,我们项目课题就走得很快,因为我对他们有信心,他们自己也知道有信心,不会随便被我否定,所以你们化学的技术也是有用的。另外,我也弥补了短板,我认为我们现在肯定有很重要的工作,而且不止一个。王鸿飞:那你刚才讲到,你是有Tenure的,所以不用担心钱。那我们有很多年轻PI还没有Tenure,他应该操心些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你当年是怎么做的?饶毅:我先得认错,你刚才说因为有Tenure所以有钱。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说是因为有Tenure,而且有研究经费。王鸿飞:有了Tenure就有钱了?饶毅:不一定,它们是两个事情。很多人其实是在独立前几年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做得很漂亮,做得很好。年纪大了以后做得好的人不多。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Avery(艾弗里),洛克菲勒的,年,他是64还是65岁做出的工作,是比较少的年纪很大才做出重要工作的人。他后来没有得诺贝尔奖,因为他心脏病死了,年纪大了。在中国的情况下,在西湖大学情况下,其实年轻人应该就开始做特别好的工作。我认为年轻就可以做,而且大家知道做得厉害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Tenure之前做的重要工作。Tenure之后做重要工作是有,像我这么大年纪,或者你这么大年纪,再做重要工作,全世界是比较少有的。王鸿飞: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做TenureTrack时,就应该去做一些冒险的东西?饶毅:我觉得非常值得,我觉得同学也是这样,因为现在中国的生物产业,这是第一次小起飞了,所以我们现在同学不用担心职业问题。第3段短视频(赛先生):《为什么“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句话是对的?》饶毅:过去有30年,里面有20多年学生物的人和他的家长、中学老师咒骂生物学,说从某某某到施一公老师,前赴后继忽悠大家“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搞得大家都没有前途了。这个批评是不对的,因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句话从来都是对的。而且是物理学家说的,不是生物学家说的,是说在自然科学里面,生物学发展的是最好,而且越长越大,这在过去40年里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连化学家都把生物当成化学了。在世界上,特别在我们(那时)读书的国家美国,生物技术的产业也起来了。对这句话意见,原因是因为大部分华人认为这句话意思是说,学了生物就能赚钱,人家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意思,它没有跟自然科学之外的学科比较,它是学科比较,21世纪的科学,不是21世纪的职业,不是与金融、唱歌、卖货来比,没有这样比过。现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也起飞了,所以这句话现在在中国是完全满足了,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再批评了,逐渐更多华人也能接受。视频:01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形成了第一个小高峰,以后会掉下来一部分,再会上去,再会下来。生命科学在中国突然一下变成柳暗花明,在各方面都前途很好。我是回答什么问题谈到这里来的?王鸿飞:我都听入迷了!其实我的感觉是说,很多学科发展了一个阶段,会到一个瓶颈,这个时候我们在选择进入什么学科,我说的不是那么大的学科,是稍微具体一点的学科。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做什么样的问题。另外对于诺贝尔的问题。我自己的选择,实际上从我做研究生时开始,就专门去找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领域,我的领域就是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一些领域开创的人还在那儿等,不知道你的建议是什么,你的认识?饶毅:我生物学大部分领域都没有做完。什么意思呢?当一些技术可以用的时候,这个领域有进展,然后到了技术的极限又做不下去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过一段时间(甚至很久)后有新技术又可以再研究,所以留下一大堆没有挖完的坑。一大堆没有挖完的坑,你需要决定永远是跟着现在热门的坑,跟着杂志的编辑的兴趣,还是自己找问题。你可以找一个明显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很长时间没有人做了,找这种冷点,然后看现在的技术能否重新启动新阶段的研究。我实验室就干了一个这个事情。年到杭州来给一个学术报告,准备了《神经科学年》。我写写写就发现,原来神经递质这个领域,在70年代停了是技术原因。多巴胺是神经递质之一,是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之间、神经细胞和靶细胞之间的化学递质,绝大部分在我开始读大学之前都“做完了”,觉得自己生得太晚了,没有机会,只能跟着别人后面,多巴胺怎么怎么重要。我在讲那个课时,年龄足够大,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假死“的领域,因为当时能用的方法全用光了,就停在那里。一个什么明显的漏洞,神经递质有外周的,也有中枢和脑里面的。乙酰胆碱作用于肌肉,去甲肾上腺素也是跟心血管、肠子、平滑肌,都是外周的,70年代以前的递质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外周生物反应找到递质分子。中枢的脑这么大,凭啥它的分子要对外周系统有作用呢,可以少部分中枢分子在外周也有作用,而大部分只在脑里有作用。我想通了这个问题,推断脑里肯定有新的神经递质分子。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想,怎么找,技术试了很久,而且试了不同的路径。9年来走了很久很久,试了不同方法,克服困难,最后我们肯定做下来了。我们做下来之后就知道,生物化学和化学对于神经递质,都非常重要,脑里面可能还有以前没有想到、甚至不知道的化学分子。我们年做到现在,做了9年,磨了好几个学生,但他们肯定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今年突然世界某个名牌大学一个GoldenBoy,一家人都是很厉害的科学家,突然发了一个文章,说他找神经递质。我想终于还有一个也能想到我们能想到的想法,紧张了一下。一看位置,他们的生物化学比我们差的太远了,他们说没找到这个,没找到那个,说明这些东西都不是。那天我们肚子都笑痛了,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生物化学技术不够好,我们想到了问题,还要把技术搞好,要不然也不用坚持了九年。我学生九年、十年才发一篇文章,西湖大学以后应该化学系取一个,生物系取一个做老师,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Pioneers。王鸿飞:你讲了这些,我倒是明白了几件事情,很多人都跟我讲,饶毅不懂技术,也不重视技术,看你刚才讲,你只是不懂技术,还是很重视技术的。---------------------------第三部分长视频(知识分子)《关于什么是好的大学》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研究方面的事情,但西湖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单位,尽管我们要做一流的研究。另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大学。大学来讲,大学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大学里存在着知识传承的问题,也存在着发展新的知识和新的研究的问题,那你对西湖大学教育方面有什么想法?饶毅:我觉得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核心肯定是老师和研究,第二是学生和教育。我觉得这个得说清楚,不能说学生是核心,研究型大学核心不是学生,是老师。但是我认为教育非常重要。我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也应该好好做教育。我自己做教育和鸿飞一样,我们都是做教育的典范,我为学生写教科书,所以我的教育肯定做得很好,因此不能说教育就是第一,教育还是第二。小型的大学做教育是相对容易的,我们招老师的时候,有一批老师就是研究好,管他教学好还是不好,都要他。但我们同时再招几个教学好、热心做教学的老师,鼓励这些老师好好给学生传承。但对于老师是不是拿Tenure肯定不重要的,这个也是得讲清楚。我这里跟老师说一下,我有一个课题完全是讲课讲出来的,我讲课时花了很大工夫想这个事情,而不是看教科书随便抄一点东西,我在想这个事情。想这个事情时,就想通了这里有问题,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意识到重要的问题,教学和研究可以互相促进。非常值得重视做好教育,但不是逼每一个老师都教课,有一部分老师教课好就可以了。王鸿飞:你认为学生受的教育和他接受的,他所从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传统的教育是灌输型的,现代的教育应该不是灌输型的。饶毅:我觉得灌输型教育很有用,中国经济起飞就是灌输型教育的很大成功。但在模仿和学习成功之后,我们肯定要走下一步。我们要更注重创造性,西湖大学肯定要以这个带头。其他学校,考试要总分,这就是扼杀了很多科学天才。而我们西湖大学现在大部分是研究生,不用担心,像生命科学这种研究,大部分智商都是很低的,人家学化学的人都看不起我们学生物的人。但它有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有重要的工作。聪明的人可以做得非常好,笨的人也可以做得非常好,数学、物理太聪明的人学生物,这是自杀,生物用不着数学的IQ高的来凑热闹。但需要理解生物学问题,在生物里面聪明的人三个月能搞清楚的事情,蠢的人六年也能搞清楚。因为问题只有那么多,翻来覆去看来看去都搞懂了。生物学可以是不同特长的人都能在里面做。而且现在也不一定都要做实验好的,做实验不好去做生物信息学,也能做得挺好,每个人可以发挥不同的特长。我们的学生在某个实验室课题不行,可以换课题。在某个实验室不行,可以换实验室,现在西湖的学生又多,特多,可以换实验室。甚至有时候跟化学的人学一点东西又回来,也是有可能。我觉得每个学生要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继续培养自己,也要找到自己特长,用好自己特长。我希望西湖的同学对于做自然科学和工程也要高兴,你们千万不要去学很多以前的家长老师,华人家长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做什么就说什么东西又苦又累又没有回报,都让自己的孩子学生不要干这一行。这是瞎说。这些人都没有对领域进行过比较。我女儿很聪明、学习成绩优异,但她学电影导演,那才是苦的要死又没有回报,做生物比那容易多了。做科学实验是一个相当稳定的职业,你只要做得还好,下一步都在等着你。文科的人从25岁到40岁,恐怕不知道在世界上自己是干什么的。因为文科的东西谁都会。理工医农,学了可是一步一步、很稳定的职业。这么稳定的职业,你还要想立马有很多回报,简直就黑了心,风险低的行业回报就应该低,风险性很大的行业需要有较高回报才能平衡。在实验室根本不算工作苦,在实验室的人还不如在金融界的那些人,那些人才一天到晚跟外面的人竞争、跟自己团队的人竞争。而你没有跟谁抢,花的工夫也不大。真正苦是在农村种田的,你们也没有一个人去种田,在这里做科学就是非常舒服的,千万不要抱怨。如果热爱科学,会非常enjoy。第四部分长视频(知识分子)《如何获得终生教职?》王鸿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年轻的PI更关心的,你对他们的Tenure这些有什么建议,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因为这个做法在我们中国是比较少的,而只有北大和清华现在在开始尝试,我们西湖应该怎么做?饶毅:除了“两校”以外,其他学校逐渐都在做了,只是不容易做好。因为“两校”主要依赖国际同行评估,我想西湖以后大概也会这样。其他的学校,外国人可能不愿意给你评估,中国这么多学校,评估又没有劳务费,累的要死。这个事情既难又容易,容易是说你能在哈佛拿到Tenure,肯定在西湖肯定也能拿到Tenure。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与哈佛一样,一定是逐渐水涨船高。西湖只要招的人越好,Tenure的标准一定会提高。它招不到人,只能把Tenure标准降低,挽留大家。它招到更好的人,一定把标准拉高,这是自然客观合理的过程。王鸿飞:所以你觉得评Tenure容易,还是评诺贝尔奖容易,或者是评什么“突破奖”容易?饶毅:当然评大奖容易,因为大奖给的人数很少,这个线很容易划,多刷几个人没有关系。评Tenure难很多。北大整个全校tenuresystem都是我们这一批人起了很重要作用,包括田刚、汤超、陈十一、谢心澄、张东晓、晓亮等,在标准上起了很大作用。我们都还回北大参加评审参加,这对北大很重要。凡是通过这个体系评审的老师会珍惜这个职位。而如果不是这样评上来的,参差不齐。在中国的情况下,有些很差的人拿了一大堆经费,甚至还拿了一大堆Papers。有些单位的领导搞不清楚他们行不行,但我们有国际同行的评审,对把握标准非常重要。王鸿飞:所以我们围绕做什么样的研究。饶毅:我这样举一下例,我们北大、清华做生命科学的,清华有发了Nature,拿不到Tenure的。北大有Paper很少很少但拿了Tenure,而且很多人觉得他的工作做得很重要,不是简单用文章而是做了什么研究工作,同行是不是足够重要,是不是有足够的努力。王鸿飞:这个我知道,北大化学系一位教授文章很少,引用很少,也拿到Tenure的。饶毅:这是说好还是坏?王鸿飞:好啊,因为你敢这样做,不是为了降低自己水平才这么做的。饶毅:这主要是理工科做得好。另外,我们在老的学校里还有一个事情,是消灭了“近亲繁殖”。“近亲繁殖”不是老师学生在同一个学校一定不行,而是学生第一肯定要做得好;第二,最好和老师做得不一样,第三以后要独立于原来的老师才行。其他不应该留下。很多学校留了一堆学生在自己院系里,我们起了很大作用把这些给砍了。有个学院院长是新来的,汇报完了意识到有候选人要被砍了,院长快哭出来了,觉得这不得了,回去怎么办。后来我和他说,你的领导以前也在这个委员会上,他砍别人时一样砍的,你也别担心。----------------------------第五部分长视频(知识分子)—问答环节王鸿飞:今天两个主题非常好,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不过,现在是科学和伪科学,在中国从来没有讨论过标准是什么,现在我们有时候指控一些科学家搞伪科学,你对科学和伪科学的标准,这是一个问题。饶毅:这有几层,伪科学一般常常是非科学界的一些人,做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号称是科学。还有一部分,科学规范问题,我们中国有一堆人科学不规范,作假,目前也比较多。作假一种是赤裸裸的作假。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其他原因。另外,有些人做的科学不严谨。老师理解不深、标准也不严。中国科学家最近声誉出现问题,主要是一些老师投稿了之后,审稿人意见回来,作者都拿得出结果应付审稿人。审稿人知道有些结果是不太可能的。现在中国一批年轻的老师,问什么问题都回答的出来,人家没有办法不接受你的文章,但心里并不信这样的结果。我们西湖的不要跟这些人有些很有名,但不是我们西湖学生的榜样。我们的榜样是真正对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王鸿飞:我补充一下,你刚才讲到的学术不端,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像当年Langmuir讲的问题,他有一个词是“病态科学”,pathologicalscience。看起来像是science,但最后得到的东西又是经不起考验,似是而非的,那样的东西反而是现在做研究里问题更大的东西,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第四段短视频(赛先生)《该如何理解“意识是否物质的?”》学生提问:饶老师你好,我想问两个神经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在我心里想的比较多的,我们都知道记忆是有时序性的,大脑可以通过强化的学习产生永久记忆。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会做梦,梦的又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梦境。这个梦境,我只做一次梦,但可以产生永久记忆。我小时候做的一个梦,时常想起来,但我只做过一次,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关于大脑的意识,您认为意识是物质的吗。如果是的话,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命题。我是生科院,级的。饶毅:这些问题都很有趣,但都没有答案的。记忆如何形成不清楚的,大家研究的是重复性刺激产生的记忆。一次性事件产生的记忆,很少人研究。你其中一个问题,虽然发生了一次,你也许是自己回顾过很多次,那就等于发生过很多次,你在不断回顾。真正单次刺激的记忆我不太懂。意识肯定是物质性的,我不认宗教。意识是物质性的,都是物理原理、化学的分子。神经冲动全是依赖电荷,意识肯定是神经冲动所组成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组成的。我们化学分子在物理原理上进行运行,没有问题,肯定是这样。但怎么样形成意识,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研究意识的人也少。最好是动物里面有才好好研究。动物里面有没有意识,有争议。另外是怎么定义,如果有实验方法定义它,就好研究。没有实验方法定义它,不好研究。神经生物学大部分问题,目前要么没有研究,要么研究的很粗浅,所以神经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里最大有可为的领域,你们都应该报考神经生物学。提问:饶老师你好,我们知道施老师学有所成之后在西湖大学当校长,您学有所成之后在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印象,学而优则仕。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本有岗位上,比如说施老师在清华大学副校长岗位,在他的实验室帮每一个学生编写好每一本教材,上好每一堂课,去发挥他的力量。而是要去做一些创办西湖大学,做这种事情?饶毅:我觉得每个人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既能做研究教学,也能做行政。我看过很多人之后,我认为施一公的创造和领导能力非常强的。我也认识一些科学和他差不多,很好的人,我觉得领导能力是达不到这个程度,做不了这个事情。要创办一个大学,在中国创办一个全新的研究型大学是极端难的,需要很多因素。你说的另外可能性也是都有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行政了。我以前一共只做过6年的院长。我后面的“行政职位“全是假的,不是正式的行政职位,只是一个头衔放在那里,没有具体任务。最近让我去做一些工作,有可能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本身还有很多问题。生物已经走了很远,医学整个教育体系走得很慢,这时候能不能帮助促进带动一下,值得努力。王鸿飞:我的总结,他们是有理想,有vision,然后又愿意做奉献,他们实际上是在做奉献,像我的话就不做领导。饶毅:他老早就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鸿飞:最后证明是失败的。提问: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看博客和